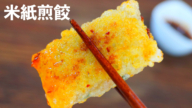“整风”,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2]]共产党自称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国家,既然要整顿党的作风,而且要“开门整风”,邀请“领导阶级”工人和农民提意见才是正途。可是被邀请批评共产党的,恰恰不包括工人、农民。被邀请“帮助党整风”的仅限知识份子、民主党派。为什么这样安排?为什么毛泽东对工人、农民的批评不感兴趣?
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知识份子属于剥削阶级:
(中国有两个剥削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
第一个已被消灭,对第二个怎么处理?在决定整风后的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上,毛泽东是“出这么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它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挪到他父亲哪里就要打屁股。”
原来,被邀请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正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的“第二个剥削阶级”!
那么,毛泽东这么做的个中奥妙是什么呢?他所说的“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指的又是什么呢?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度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原匈共第一书记拉科西下台。十月,匈牙利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说,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俄国人滚回俄国去!”几十万人聚集国会广场,并拆除了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
开到国家广播大楼前的摩托部队被示威群众缴械后,广播大楼、国际电信局、匈共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相继被示威者攻占。匈共中央紧急改组,一年多前被罢免的总理纳吉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
苏联坦克部队开进布达佩斯后,纳吉主持的匈牙利政府与苏共代表谈判。匈牙利共产党解散,重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苏军撤出后,群众对共产党和保安警察展开报复,杀了两千多人。纳吉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宣布匈牙利中立,并希望联合国干预匈牙利事务。苏军坦克再次攻入布达佩斯。纳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关押处死。大逮捕席卷匈牙利。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198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占据毛泽东头脑的是阶级斗争、巩固政权的问题。在十一月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3]]在一九五七年一月间的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都作了长篇讲话,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反右斗争,不可不读此一讲话:
“思想动向的问题:党内思想动向、社会思想动向应该抓住。”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丁注:指赫镇压了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马列主义了],蚂蚁也缩回去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4]]
“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没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再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5]]
“要不犯路线错误,(就)不(会)出全国性乱子。即使犯了路线错误,全国大乱,占了几省几县,甚至打到北京西长安街,只要军队巩固,我们也不会亡国,国家会更巩固。”
“小资产阶级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它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让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这里所谓的“他”,正是五个月后被从六亿人中孤立出来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就像“三反”时他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指定全国“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一样,毛泽东又事先设定了指标: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
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全国二十余省市,大中小合起来近一百万。后来被定为“极右派”、“右派”、“中右分子”的,果然有一百万。而且没等到年终,在年中六月就“结账”了。
当时,毛泽东连什么人将是右派也已经有点谱了。他提到了萧军、丁玲:“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6]]半年后反右,萧、丁二人都是“大右派”。
由此可知,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占据毛的头脑、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国“党内外”那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对毛来说,那些“缩回去的蚂蚁”是潜在的威胁,不清除它们,他在紫禁城那个黄圈圈里就睡不安稳。波兰、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动告诉他,知识份子鼓动工农造反,推翻一个昨日还貌似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毛泽东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去苏联,指示他们“劝说苏联同志”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7]],匈牙利共产党政权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他告诉各省、市委书记们:
“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
此时,他所谓的“争鸣”不是学派间的争论,而是鬼子、王八的聒噪。他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层面,成了“鸣放”。所以,在反右后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不无得意地说:
“鸣放是我们发明的。”
“鸣、放”二字取自学术、文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本与政治不相干。而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的“鸣放”,却是给共产党提意见,已与学术、文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关。这纯是毛泽东引导的结果。
他自然明白如果他的讲话传播出去,这政治上的“鸣放”是搞不起来的。所以,在对中、下级干部讲话时,上面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词都不见了: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8]]“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9]]“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得心应手地推动这个政治上的鸣放。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层层传达,告诉全国:毛主席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三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对党外人士谈吐温和地说:
“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当然没有事,言者无罪嘛!”
“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
“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
“蒋介石他讲了很多东西……我就赞成出全集。”
他将全国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请到北京,听取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录音,听他说:
“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希望党外朋友帮助。”
“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10]]
三月十日召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他的态度特别谦逊:“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当党外人士、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试探地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毛答:“你的意见很对、很好。”[[11]]
那时,毛泽东只要提及“双百”,就一定与政治上的鸣放联系起来。而且仅限于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对中共的鸣放。他说:
“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份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12]]
从他把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当做“很不好看的花”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百花齐放”与文艺、学术毫不相干。但是反右以后,他不仅矢口否认,且倒打一耙说:
“我们去年五月在这里讲百花齐放……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不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大鸣大放。”[[13]]
“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的,他们要用于政治。”[[14]]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15]]
在将其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他干脆删去“鸣放是我们发明的”这句关键的话,否认了“鸣放”是他一手策动的。
毛泽东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的讲话不会传播到徐铸成们的耳朵里,说话不必忌讳,无需文质彬彬。所以,在四月上海局杭州会议上,杀气腾腾的言词又回来了:
“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有些知识份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
“我们主张放,最大坏处无非是乱一阵。……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反对肃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16]]
在杭州开会时,浙江省委问毛泽东:“最高国策、最高领袖可以不可以批评?”毛回答“不能答不能批评”,但接着就以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例,说:“合作化能不能批评?要批评可以登一篇,然后来一个反驳。一驳就臭了。他反对合作化就有证据,等于照了相。这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他自己钻进来的。”[[17]]显然,毛泽东和他制订的国策不可以批评,谁批评谁就是“自投罗网”。
这种话当然不会透露给公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却看透了毛指令党的宣传喉舌为鸣放推波助澜的用心。据副总编辑胡绩伟说:
“(邓拓)比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阴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18]]
三月十九日,从天津、济南到达南京的毛泽东自称“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19]]但毛南下未予公开,人民日报对他的一路游说也就没予报导。邓拓警告部属“不要锣鼓一响就出来”。代表毛泽东领导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也支持邓,不刊登毛泽东游说期间的讲话。为此毛泽东大为愤怒,四月十日,他将邓拓、胡绩伟、王若水等人召到自己的卧室里训话。他躺在床上,“像训斥孙子似地”[胡绩伟语]训道:“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20]]他又骂邓拓“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同时,还斥责几位副总编辑“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21]]
起先,对于要不要刊登批评共产党的言论,人民日报编辑李庄拿不准。请示邓拓,他也不敢擅自作主。过了几天,他突然对李庄说:“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记者都派出去,这一段就写这种稿子。”从来没见过党报发表“反动言论”的李庄不明白对为什么这样做,却也“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22]]
解决了人民日报对“放”的顾忌,还得解除知识份子的疑虑。毛知道知识份子被“阶级斗争”搞怕了,于四月十一日将北京大学冯友兰、贺麟,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等十多人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我们党对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23]]
在场者没一个知道毛正在谋划“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更不知道二十天前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份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24]]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又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上天安门城楼,说:
“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儿去讲,人家[指教授──丁注]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25]]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毛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令许多人耳目一新,以为从此百无禁忌,“不平则鸣”、“有气则放”就是了。
当时,有些党内的高级干部也被迷惑,以为毛泽东要搞“改革开放”了。善于观风、跟风的马上做出反应,表示支持。副总理谭震林听到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26]],以为开放报禁、允许党外人士办报将成为党的政策。他跑到湖南,学毛泽东骂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的腔调,骂新湖南报是“死人办死报”,说每省可以办两份报纸,一个由党外办,唱对台戏。
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见毛泽东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也以为要改革了。他跑到清华大学,与校长蒋南翔讨论“教授治校”的问题。五月初蒋南翔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对校党委传达:“教授治校问题可能要考虑,党委制是否可行,请(邓)小平同志考虑。”十一日,蒋南翔与陆定一谈话时,也谈了“在高等院校是否实行党委制应该缓行”[[27]]的意见。
其实,毛泽东关于学校党委制和“每省办两个报纸”的讲话全是哄骗。不久,他就转了个一百八十度,说:“章伯钧、罗隆基等……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28]]于是,对学校党委制发过议论的人,统统是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因为他说过“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29]]西南农学院教授蒋同庆不赞成“教授治校”而主张“教授治学”,也是右派!
而那些请中共允许各党派自己办报、办通讯社的人,一个也没逃脱右派帽子。杨秀峰、蒋南翔、谭震林只是虚惊一场,白忙一阵。
毛泽东从未打算“改一下”学校党委制,这是显然的。他若真认为每省党内党外各一个报纸好,反右后完全可以办。可是以后的二十年间他再也没议过此事。
毛在施政大事上绝不容他人置喙。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会议上,与毛同龄、常被毛请去作客的学者梁漱溟对中共靠剥夺农民积累资金搞重工业的办法提出异议,毛当场翻脸,将粱臭骂一顿,用词不堪入耳。随后发动了“向粱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的运动。
毛泽东骂粱漱溟时,曾承认自己“没有雅量”接纳意见。如今突然礼贤下士,对于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实在是新鲜。过去几年,他们只是改造对像,自我批判,互相揭发,台上斗争,台下检讨,早不敢想像自己有资格批评共产党。如今共产党突然邀请他们批评,第一个反应就是: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文章?
费孝通教授写了一篇《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请女作家冰心等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里,北大教授翦伯赞写了篇短文,谈到知识份子“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30]]
在知识份子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人们注意着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什么主意。”因此,“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原因……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是分不开的。”[[31]]
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也表示有顾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该校一位教授干脆问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将来会不会再来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再来整我们一下?”[[32]]
在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民盟副主任陈仁炳将人们的担忧、顾虑归纳为“六怕”:“一怕报复打击;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像是不倒翁;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怕被领导认为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上批评你是在算旧账。”[[33]]
复旦教授王造时说:“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们可以摸出这么一个鸣放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鸣放……越到乡村,越不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最弥漫。”[[34]]他建议中共采取实际措施保证言者无罪:“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35]]
在中国人民银行非党干部座谈会上,朱绍文说:“这几年来知识份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36]]
对人们为什么欲放无胆,东北工学院教授许冶同在校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向领导提出批评者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和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较密者被认为“反动小集团”,在肃反时都成为斗争的对像,肃反后都成了惊弓之鸟,甚至六亲不认,相对无言。所以在此次会上,不愿发言,恐自取其咎。因为有了过去沉痛的教训,免致重蹈覆辙。”[[37]]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穆木天说:“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怕再遭一次无妄之灾。因为在师大,教师被发配、降级等等之类的阴谋报复,是早有前例的。”“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师大几年来一贯的传统。”[[38]]
有人不相信共产党会真正实行“言者无罪”。有的人甚至明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铁券是过去皇上保证不对功臣加罪的誓言。[[39]]所以,说话者只是表示怕被加罪,并不真的企求一张铁券。
河南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倒像隋炀帝。”“破格用己,妒贤忌能,以顺为贵,以直为仇。”[[40]]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广州《工商周刊》编辑樊建华在谈论人们为何不愿鸣放的文章中引了这两句唐诗,道出了多数知识份子的心声。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的经历记忆犹新,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声明坚决“不跳”。有位教授在家里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重庆一位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议论,吃够苦头后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有的教授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悄悄劝人道:“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41]]
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也认为情况异常:下个文件,表一下态就够了,何必盛词大噪,千呼万唤?为何其鼓动对像都是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他疑心“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不过,对于不少人采取的“三缄其口”的作法,他也担心未必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42]]
在五月九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整风座谈会上,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但是,大多数民主党派的头目却相信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意。他们积极出面鼓励各界“帮助党整风”。五月十二日,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建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带头鼓动工商界鸣放:“工商业者应积极参加争鸣……提意见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客客气气,不要怕戴帽子,不要怕打击报复。”[[43]]
二十二日,在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说:“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想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的大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以后再整?”[[44]]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说:“有人提出要党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议在全国各级政府设立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还主张这个委员会除共产党外,也让党外人士参加。[[45]]
其实,早在龙云说共产党不会“开这样大的玩笑”之前一个星期,鸣放才刚开始,绝大多数人还没开口,大字报还没出现,毛泽东就已经在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抓右派运动了。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说: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46]]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明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其“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安排:“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47]]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名为《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的文件,说:
“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48]]
五月二十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点是:
“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在一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49]]
据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从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愈嚣张愈好’”[[50]]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示各省市委书记:“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51]]
“反右派的信号”[[52]]至迟是在五月十八日发出的。那天晚上,《文艺学习》编辑黄秋耘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励他“大胆地放”时,周扬来了电话。听了电话,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放下话筒对黄说道:“唔,转了!”并嘱咐道:“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53]]
周扬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主管之一。可以推断:周扬绝无斗胆破坏毛的部署,他一定是从毛处或其他最高领导人处得到了指示或暗示。
五月十八、九日,党委书记们或者获得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容,或者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或二者都收到。据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伍宇回忆,作协在“五月十八、十九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将《事情正在起变化》“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伍宇是听到传达的少数人之一。[[54]]
除了报纸,全国的广播电台也在为“秋后算账”准备材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局党组会议上传达中央指示,说:“对右派的言论可以照登,过一个时期,等中央有通知再来个反击。”[[55]]
李维汉身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自然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容。他后来也说:“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56]]当然,他没有将一个字透露给与会者。座谈会还是每两天开一次,一直开到六月三日才中止。
龙云、罗隆基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立即见了报,惟独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发言未被报纸刊出。他表示不解。上面暗示他:“你那个发言有错误,现在不公开发表是对你的爱护。你要汲取教训。”他才弄清座谈会背后的玄机。
知道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容后,许多原先消极应付中央“鸣放”指示的干部一下子放了心,积极领导起“鸣放”来。他们甚至逼迫群众鸣放:“谁不参加鸣放,谁就是对党不关心、不爱护,不爱社会主义……”
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是个例外。他未报告省委即擅自把《事情正在起变化》向市委、市政府中的党员副局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后来,那些听了传达的干部没一个成右派。[[57]]当然,对党外干部和副局长以下的党员干部他就没有胆子透露一个字了。
五月十九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到中山大学与教授们座谈了六个小时。会上,当中文系董每戡说到学校大部分党员“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时,陶铸插话道:“是冷若冰霜。”董接着说这些党员“运动一来拚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陶铸表示,党组织是不会报复谁的,要大家不要怕。[[58]]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是得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内容后立即转向的干部之一。五月二十一日,他给全校作报告,鼓励大鸣大放。二十四日上午,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中午,蒋发表广播演说,鼓动学生用各种形式鸣放:大字报、辩论会、自由论坛、演讲、访问教授均可。校青年团委及学生会表示马上开辟“民主墙”,供同学张贴大字报。二十七日,蒋南翔出席物理教研组的鸣放座谈会。教员何玉骐不知道蒋已经转向,会间指着他说:“党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你就是其中一个。”会后,蒋指示教研组党支部书记陈纲,把会议报导送校刊发表,称鸣放会“乌烟瘴气”。教员们指斥陈纲,陈供出了奉蒋指示炮制该文的背景。不久反右,不仅鸣放的教员都是右派,连陈纲也因“出卖了领导同志,出卖革命机密,泄漏了党委‘暴露右派’的作战方针”,成为右派。[[59]]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两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把清华大学党委、团委、各系的负责人召去,布置继续鸣放。[[60]]他还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的党委书记去谈话,要他们用各种办法,制造气氛,引蛇出洞。要他们示弱,使右派们尽情鸣放,无所顾忌。并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61]]
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在社内号召“四完”:“有意见提完,有批评提完,有气出完,有冤伸完。”[[62]]辽宁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李荒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有话放出来最好》,鼓励人们“大胆放,大胆鸣”。吉林省委将一所大学的礼堂改名为“鸣放宫”,郑重其事地请书法家题了匾额。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针对有人说中共是
“先放后收再整”,向大家保证:“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永远是放。更不会被整。”[[63]]
五月二十五日,周扬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64]]陆定一在中宣部的大会上带头鸣放:“党没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
基于“暴露右派”的谋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几乎天天给文汇报发指示,要该报为鸣放加温再加温。五月二十五日,不明底细的总总编辑徐铸成召集报社编辑部全体大会,传达柯的指示,说:“体会柯老的话的精神,现在仍然是要鸣要放,而不是收。”[[65]]
春风吹到玉门关。中共的诚恳态度终于收效,人们解除了戒心。
中共似乎已经改弦更张,真的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了。名画家林风眠写了一篇文章,称毛泽东的讲话,“好像度过了漫长的冬季,送来了第一阵春风。”一位教授万分感动地说:“争鸣这个方针的提出,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党和毛主席真是伟大﹗”
人们都忘了“双百”,只记得“鸣放”了。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人人说鸣放,家家谈鸣放,说的谈的都是政治上的话题。
五月三十一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剧作家吴祖光出席一个小型鸣放座谈会,而且特地派人派车去接他。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他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新凤霞却忧心忡忡,不肯放行。她不让吴祖光去会上提意见。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那也不许你提﹗”
事后,吴祖光不无后悔地回忆道:“我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66]]
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吴祖光不仅是右派,而且还是个“反革命右派分子”。
但那是反右运动开展以后的事了。而在五月那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许多人都像吴祖光一样,相信了毛泽东说的话。
上海电影女演员吴茵到北京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她对毛的诚意深信不疑,对还打算看看风向的伙伴说:“怕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写,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67]]她哪会知道,她也是个小蚂蚁。不久她就成为上海的一名“大右派”,被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去了。
在循循善诱的气氛中,人们嘴上的闸门终于打开了。闸门一旦打开,心中不满淤积已久的人民就不那么温文尔雅了。“鸣”成了“鸣鼓而攻之”的“鸣”,“放”字成了“大放厥词”的“放”。
五月四日国家计委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时,四十年后成为中共总理的青年干部朱镕基说:“大家还等什么,还怕什么?……还不相信党吗?我就什么都不怕,就要讲真话、讲心里话,给党扫扫灰尘。不然灰尘积了太多、太厚,要用铁铲、铲车来清除。”[[68]]
这是绝大多数鸣放者的心声。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人民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广泛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规模空前。不过这局面仅维持了一个月,之后就是同样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当毛下令“反右”时,他们夹紧尾巴也来不及了。鸣放者几乎都成了“右派分子”,朱镕基只是其中之一。
注释
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69]]
第一个已被消灭,对第二个怎么处理?在决定整风后的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上,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出这么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它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挪到他父亲哪里就要打屁股。”[[70]]
原来,被邀请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正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的“第二个剥削阶级”!
那么,毛泽东这么做的个中奥妙是什么呢?他所说的“他们的子弟要学匈牙利”,指的又是什么呢?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度被称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原匈共第一书记拉科西下台。十月,匈牙利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涌上街头,散发传单和演说,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俄国人滚回俄国去!”几十万人聚集国会广场,并拆除了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
开到国家广播大楼前的摩托部队被示威群众缴械后,广播大楼、国际电信局、匈共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相继被示威者攻占。匈共中央紧急改组,一年多前被罢免的总理纳吉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
苏联坦克部队开进布达佩斯后,纳吉主持的匈牙利政府与苏共代表谈判。匈牙利共产党解散,重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苏军撤出后,群众对共产党和保安警察展开报复,杀了两千多人。纳吉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宣布匈牙利中立,并希望联合国干预匈牙利事务。苏军坦克再次攻入布达佩斯。纳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和“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关押处死。大逮捕席卷匈牙利。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198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初,占据毛泽东头脑的是阶级斗争、巩固政权的问题。在十一月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71]]在一九五七年一月间的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开始和结束时,毛都作了长篇讲话,要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反右斗争,不可不读此一讲话:
“思想动向的问题:党内思想动向、社会思想动向应该抓住。”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丁注:指赫镇压了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马列主义了],蚂蚁也缩回去了。”[[72]]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73]]
“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没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再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74]]
“只要不犯路线错误,(就)不(会)出全国性乱子。即使犯了路线错误,全国大乱,占了几省几县,甚至打到北京西长安街,只要军队巩固,我们也不会亡国,国家会更巩固。”[[75]]
“小资产阶级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它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让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76]]
这里所谓的“他”,正是五个月后被从六亿人中孤立出来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就像“三反”时他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指定全国“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一样,毛泽东又事先设定了指标: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77]]
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全国二十余省市,大中小合起来近一百万。后来被定为“极右派”、“右派”、“中右分子”的,果然有一百万。而且没等到年终,在年中六月就“结账”了。
当时,毛泽东连什么人将是右派也已经有点谱了。他提到了萧军、丁玲:“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78]]半年后反右,萧、丁二人都是“大右派”。
由此可知,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占据毛的头脑、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国“党内外”那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对毛来说,那些“缩回去的蚂蚁”是潜在的威胁,不清除它们,他在紫禁城那个黄圈圈里就睡不安稳。波兰、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动告诉他,知识份子鼓动工农造反,推翻一个昨日还貌似强大的共产党政权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毛泽东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去苏联,指示他们“劝说苏联同志”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79]],匈牙利共产党政权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他告诉各省、市委书记们:
“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80]]
此时,他所谓的“争鸣”不是学派间的争论,而是鬼子、王八的聒噪。他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层面,成了“鸣放”。所以,在反右后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不无得意地说:
“鸣放是我们发明的。”[[81]]
“鸣、放”二字取自学术、文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本与政治不相干。而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的“鸣放”,却是给共产党提意见,已与学术、文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关。这纯是毛泽东引导的结果。
他自然明白如果他的讲话传播出去,这政治上的“鸣放”是搞不起来的。所以,在对中、下级干部讲话时,上面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词都不见了: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82]]“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83]]“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84]]
毛泽东得心应手地推动这个政治上的鸣放。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层层传达,告诉全国:毛主席说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三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对党外人士谈吐温和地说:
“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当然没有事,言者无罪嘛!”
“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
“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
“蒋介石他讲了很多东西……我就赞成出全集。”[[85]]
他将全国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请到北京,听取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录音,听他说:
“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希望党外朋友帮助。”
“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86]]
三月十日召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他的态度特别谦逊:“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当党外人士、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试探地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毛答:“你的意见很对、很好。”[[87]]
那时,毛泽东只要提及“双百”,就一定与政治上的鸣放联系起来。而且仅限于知识份子、民主党派对中共的鸣放。他说:
“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份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88]]
从他把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当做“很不好看的花”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百花齐放”与文艺、学术毫不相干。但是反右以后,他不仅矢口否认,且倒打一耙说:
“我们去年五月在这里讲百花齐放……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不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大鸣大放。”[[89]]
“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的,他们要用于政治。”[[90]]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91]]
在将其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他干脆删去“鸣放是我们发明的”这句关键的话,否认了“鸣放”是他一手策动的。[[92]]
毛泽东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的讲话不会传播到徐铸成们的耳朵里,说话不必忌讳,无需文质彬彬。所以,在四月上海局杭州会议上,杀气腾腾的言词又回来了:
“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有些知识份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
“我们主张放,最大坏处无非是乱一阵。……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反对肃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93]]
在杭州开会时,浙江省委问毛泽东:“最高国策、最高领袖可以不可以批评?”毛回答“不能答不能批评”,但接着就以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例,说:“合作化能不能批评?要批评可以登一篇,然后来一个反驳。一驳就臭了。他反对合作化就有证据,等于照了相。这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他自己钻进来的。”[[94]]显然,毛泽东和他制订的国策不可以批评,谁批评谁就是“自投罗网”。
这种话当然不会透露给公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却看透了毛指令党的宣传喉舌为鸣放推波助澜的用心。据副总编辑胡绩伟说:
“(邓拓)比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阴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95]]
三月十九日,从天津、济南到达南京的毛泽东自称“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96]]但毛南下未予公开,人民日报对他的一路游说也就没予报导。邓拓警告部属“不要锣鼓一响就出来”。代表毛泽东领导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也支持邓,不刊登毛泽东游说期间的讲话。为此毛泽东大为愤怒,四月十日,他将邓拓、胡绩伟、王若水等人召到自己的卧室里训话。他躺在床上,“像训斥孙子似地”[胡绩伟语]训道:“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97]]他又骂邓拓“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同时,还斥责几位副总编辑“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98]]
起先,对于要不要刊登批评共产党的言论,人民日报编辑李庄拿不准。请示邓拓,他也不敢擅自作主。过了几天,他突然对李庄说:“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记者都派出去,这一段就写这种稿子。”从来没见过党报发表“反动言论”的李庄不明白对为什么这样做,却也“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99]]
解决了人民日报对“放”的顾忌,还得解除知识份子的疑虑。毛知道知识份子被“阶级斗争”搞怕了,于四月十一日将北京大学冯友兰、贺麟,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等十多人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我们党对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100]]
在场者没一个知道毛正在谋划“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更不知道二十天前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份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101]]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又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上天安门城楼,说:
“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儿去讲,人家[指教授──丁注]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102]]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毛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令许多人耳目一新,以为从此百无禁忌,“不平则鸣”、“有气则放”就是了。
当时,有些党内的高级干部也被迷惑,以为毛泽东要搞“改革开放”了。善于观风、跟风的马上做出反应,表示支持。副总理谭震林听到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103]],以为开放报禁、允许党外人士办报将成为党的政策。他跑到湖南,学毛泽东骂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的腔调,骂新湖南报是“死人办死报”,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份报纸,一个由党外办,唱对台戏。[[104]]
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见毛泽东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也以为要改革了。他跑到清华大学,与校长蒋南翔讨论“教授治校”的问题。五月初蒋南翔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对校党委传达:“教授治校问题可能要考虑,党委制是否可行,请(邓)小平同志考虑。”十一日,蒋南翔与陆定一谈话时,也谈了“在高等院校是否实行党委制应该缓行”[[105]]的意见。
其实,毛泽东关于学校党委制和“每省办两个报纸”的讲话全是哄骗。不久,他就转了个一百八十度,说:“章伯钧、罗隆基等……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106]]于是,对学校党委制发过议论的人,统统是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因为他说过“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107]]西南农学院教授蒋同庆不赞成“教授治校”而主张“教授治学”,也是右派!
而那些请中共允许各党派自己办报、办通讯社的人,一个也没逃脱右派帽子。杨秀峰、蒋南翔、谭震林只是虚惊一场,白忙一阵。
毛泽东从未打算“改一下”学校党委制,这是显然的。他若真认为每省党内党外各一个报纸好,反右后完全可以办。可是以后的二十年间他再也没议过此事。
毛在施政大事上绝不容他人置喙。在一九五三年的一次会议上,与毛同龄、常被毛请去作客的学者梁漱溟对中共靠剥夺农民积累资金搞重工业的办法提出异议,毛当场翻脸,将粱臭骂一顿,用词不堪入耳。随后发动了“向粱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的运动。
毛泽东骂粱漱溟时,曾承认自己“没有雅量”接纳意见。如今突然礼贤下士,对于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实在是新鲜。过去几年,他们只是改造对像,自我批判,互相揭发,台上斗争,台下检讨,早不敢想像自己有资格批评共产党。如今共产党突然邀请他们批评,第一个反应就是: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文章?
费孝通教授写了一篇《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请女作家冰心等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四月里,北大教授翦伯赞写了篇短文,谈到知识份子“还在揣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放是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问题能争鸣,哪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108]]
在知识份子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人们注意着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什么主意。”因此,“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原因……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是分不开的。”[[109]]
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召开座谈会,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也表示有顾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
是要算账?”“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该校一位教授干脆问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将来会不会再来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再来整我们一下?”[[110]]
在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民盟副主任陈仁炳将人们的担忧、顾虑归纳为“六怕”:“一怕报复打击;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像是不倒翁;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怕被领导认为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上批评你是在算旧账。”[[111]]
复旦教授王造时说:“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们可以摸出这么一个鸣放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鸣放……越到乡村,越不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最弥漫。”[[112]]他建议中共采取实际措施保证言者无罪:“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113]]
在中国人民银行非党干部座谈会上,朱绍文说:“这几年来知识份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114]]
对人们为什么欲放无胆,东北工学院教授许冶同在校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向领导提出批评者就被认为对党不满和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较密者被认为“反动小集团”,在肃反时都成为斗争的对像,肃反后都成了惊弓之鸟,甚至六亲不认,相对无言。所以在此次会上,不愿发言,恐自取其咎。因为有了过去沉痛的教训,免致重蹈覆辙。”[[115]]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穆木天说:“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怕再遭一次无妄之灾。因为在师大,教师被发配、降级等等之类的阴谋报复,是早有前例的。”“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师大几年来一贯的传统。”[[116]]
有人不相信共产党会真正实行“言者无罪”。有的人甚至明说:“要我发言,先要给我一张铁券。”铁券是过去皇上保证不对功臣加罪的誓言。[[117]]所以,说话者只是表示怕被加罪,并不真的企求一张铁券。
河南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倒像隋炀帝。”“破格用己,妒贤忌能,以顺为贵,以直为仇。”[[118]]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广州《工商周刊》编辑樊建华在谈论人们为何不愿鸣放的文章中引了这两句唐诗,道出了多数知识份子的心声。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的经历记忆犹新,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声明坚决“不跳”。有位教授在家里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重庆一位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议论,吃够苦头后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有的教授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悄悄劝人道:“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119]]
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也认为情况异常:下个文件,表一下态就够了,何必盛词大噪,千呼万唤?为何其鼓动对像都是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他疑心“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不过,对于不少人采取的“三缄其口”的作法,他也担心未必是万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数百儒生,谁出过一言半语呢?”[[120]]
在五月九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整风座谈会上,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但是,大多数民主党派的头目却相信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意。他们积极出面鼓励各界“帮助党整风”。五月十二日,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建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带头鼓动工商界鸣放:“工商业者应积极参加争鸣……提意见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客客气气,不要怕戴帽子,不要怕打击报复。”[[121]]
二十二日,在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说:“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想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的大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以后再整?”[[122]]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说:“有人提出要党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议在全国各级政府设立委员会,“不但要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还主张这个委员会除共产党外,也让党外人士参加。[[123]]
其实,早在龙云说共产党不会“开这样大的玩笑”之前一个星期,鸣放才刚开始,绝大多数人还没开口,大字报还没出现,毛泽东就已经在部署全国范围内的抓右派运动了。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说: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对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124]]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明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其“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安排:“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125]]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名为《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的文件,说:
“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126]]
五月二十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点是:
“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在一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127]]
据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从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愈嚣张愈好’”[[128]]邓小平在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示各省市委书记:“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129]]
“反右派的信号”[[130]]至迟是在五月十八日发出的。那天晚上,《文艺学习》编辑黄秋耘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励他“大胆地放”时,周扬来了电话。听了电话,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放下话筒对黄说道:“唔,转了!”并嘱咐道:“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131]]
周扬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主管之一。可以推断:周扬绝无斗胆破坏毛的部署,他一定是从毛处或其他最高领导人处得到了指示或暗示。
五月十八、九日,党委书记们或者获得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容,或者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或二者都收到。据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伍宇回忆,作协在“五月十八、十九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将《事情正在起变化》“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了传达。”伍宇是听到传达的少数人之一。[[132]]
除了报纸,全国的广播电台也在为“秋后算账”准备材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在局党组会议上传达中央指示,说:“对右派的言论可以照登,过一个时期,等中央有通知再来个反击。”[[133]]
李维汉身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自然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容。他后来也说:“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134]]当然,他没有将一个字透露给与会者。座谈会还是每两天开一次,一直开到六月三日才中止。
龙云、罗隆基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立即见了报,惟独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发言未被报纸刊出。他表示不解。上面暗示他:“你那个发言有错误,现在不公开发表是对你的爱护。你要汲取教训。”他才弄清座谈会背后的玄机。
知道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容后,许多原先消极应付中央“鸣放”指示的干部一下子放了心,积极领导起“鸣放”来。他们甚至逼迫群众鸣放:“谁不参加鸣放,谁就是对党不关心、不爱护,不爱社会主义……”
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是个例外。他未报告省委即擅自把《事情正在起变化》向市委、市政府中的党员副局长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后来,那些听了传达的干部没一个成右派。[[135]]当然,对党外干部和副局长以下的党员干部他就没有胆子透露一个字了。
五月十九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到中山大学与教授们座谈了六个小时。会上,当中文系董每戡说到学校大部分党员“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时,陶铸插话道:“是冷若冰霜。”董接着说这些党员“运动一来拚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陶铸表示,党组织是不会报复谁的,要大家不要怕。[[136]]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是得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内容后立即转向的干部之一。五月二十一日,他给全校作报告,鼓励大鸣大放。二十四日上午,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中午,蒋发表广播演说,鼓动学生用各种形式鸣放:大字报、辩论会、自由论坛、演讲、访问教授均可。校青年团委及学生会表示马上开辟“民主墙”,供同学张贴大字报。二十七日,蒋南翔出席物理教研组的鸣放座谈会。教员何玉骐不知道蒋已经转向,会间指着他说:“党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你就是其中一个。”会后,蒋指示教研组党支部书记陈纲,把会议报导送校刊发表,称鸣放会“乌烟瘴气”。教员们指斥陈纲,陈供出了奉蒋指示炮制该文的背景。不久反右,不仅鸣放的教员都是右派,连陈纲也因“出卖了领导同志,出卖革命机密,泄漏了党委‘暴露右派’的作战方针”,成为右派。[[137]]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两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把清华大学党委、团委、各系的负责人召去,布置继续鸣放。[[138]]他还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的党委书记去谈话,要他们用各种办法,制造气氛,引蛇出洞。要他们示弱,使右派们尽情鸣放,无所顾忌。并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139]]
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在社内号召“四完”:“有意见提完,有批评提完,有气出完,有冤伸完。”[[140]]辽宁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李荒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有话放出来最好》,鼓励人们“大胆放,大胆鸣”。吉林省委将一所大学的礼堂改名为“鸣放宫”,郑重其事地请书法家题了匾额。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针对有人说中共是“先放后收再整”,向大家保证:“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永远是放。更不会被整。”[[141]]
五月二十五日,周扬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意见提得尖锐一点。你们太客气了,你们的批评只是一分,可是我体会到我们的缺点有十分。”[[142]]陆定一在中宣部的大会上带头鸣放:“党没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
基于“暴露右派”的谋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几乎天天给文汇报发指示,要该报为鸣放加温再加温。五月二十五日,不明底细的总总编辑徐铸成召集报社编辑部全体大会,传达柯的指示,说:“体会柯老的话的精神,现在仍然是要鸣要放,而不是收。”[[143]]
春风吹到玉门关。中共的诚恳态度终于收效,人们解除了戒心。
中共似乎已经改弦更张,真的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了。名画家林风眠写了一篇文章,称毛泽东的讲话,“好像度过了漫长的冬季,送来了第一阵春风。”一位教授万分感动地说:“争鸣这个方针的提出,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党和毛主席真是伟大﹗”
人们都忘了“双百”,只记得“鸣放”了。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人人说鸣放,家家谈鸣放,说的谈的都是政治上的话题。
五月三十一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剧作家吴祖光出席一个小型鸣放座谈会,而且特地派人派车去接他。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他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新凤霞却忧心忡忡,不肯放行。她不让吴祖光去会上提意见。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那也不许你提﹗”
事后,吴祖光不无后悔地回忆道:“我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144]]
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吴祖光不仅是右派,而且还是个“反革命右派分子”。
但那是反右运动开展以后的事了。而在五月那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许多人都像吴祖光一样,相信了毛泽东说的话。
上海电影女演员吴茵到北京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她对毛的诚意深信不疑,对还打算看看风向的伙伴说:“怕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写,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145]]她哪会知道,她也是个小蚂蚁。不久她就成为上海的一名“大右派”,被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去了。
在循循善诱的气氛中,人们嘴上的闸门终于打开了。闸门一旦打开,心中不满淤积已久的人民就不那么温文尔雅了。“鸣”成了“鸣鼓而攻之”的“鸣”,“放”字成了“大放厥词”的“放”。
五月四日国家计委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时,四十年后成为中共总理的青年干部朱镕基说:“大家还等什么,还怕什么?……还不相信党吗?我就什么都不怕,就要讲真话、讲心里话,给党扫扫灰尘。不然灰尘积了太多、太厚,要用铁铲、铲车来清除。”[[146]]
这是绝大多数鸣放者的心声。从一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人民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广泛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规模空前。不过这局面仅维持了一个月,之后就是同样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当毛下令“反右”时,他们夹紧尾巴也来不及了。鸣放者几乎都成了“右派分子”,朱镕基只是其中之一。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7页。
[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7页。
[3]《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3页。
[4]1957.1毛泽东在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7页。此文未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5]同上,《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8页。
[6]1957.1毛泽东在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10页。
[7]《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三期22页。
[8]1957.3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的讲话,戴晴《粱漱溟、王实味、储安平》(1989)194页。
[9]1957.3.17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林学院,1967)252页。
[10]《中国知识份子悲欢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225页。
[11]同上,227页。
[12]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1957.3.19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9∼1957.12)》[编者不明]158、159页。
[13]1957.10.13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63页。
[14]1958.1.28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上,93页。
[15]1958.3.25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191页。
[16]1957.4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中讨论时的插话(整理),《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42至50页。
[17]1957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大学,1967年9月)126页。
[18]1993年9月30日美洲《世界日报》,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
[19]1957.3.19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9∼1957.12)》【编者不明】153页。
[20]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199页。
[21]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22]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206页。
[23]《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五期91页。
[24]1957.3.19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党员干部会议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林学院)288页。
[25]《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47页。章伯钧在中国民主同盟传达的稍不同:“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见《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一期20页。
[26]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47页。
[27]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井冈山》报(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28]1958年1月28、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138页。章伯钧,中国民盟副主席、国务院交通部长、罗隆基;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长。
[2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30]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3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国青年报》。
[32]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33]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美洲《新闻自由导报》。
[34]《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阴谋》(编者不明,1957年7月)74至75页。
[35]王造时对记者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日报。
[36]1957.5.15人民日报,见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191页。
[37]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沈阳日报。
[38]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39]《巢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一,朱元璋敕赐俞通源铁券文:“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者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
[40]1957.8.2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219-220页。
[41]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文汇报。
[42]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327页。
[43]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红旗战报》(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4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4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13页。
[4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4至427页。
[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78页。
[4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614至615页。
[5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613页。
[51]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Thinkers Publishing Limited,2006)149-150页。
[5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89页。
[53]黄秋耘《风雨年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76页。
[54]《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期74页。
[55]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323页。
[5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835页。
[57]《任仲夷反省历次政治运动》,原载于《南方周末》,见2002.5.26《中国事务》。
[58]1957年5月21日《广州日报》。
[59]《钢与渣》(北京:清华大学团委会,1958)第六期3至5页。
[60]参加彭真召集的谈话的清华大学团委书记阮铭一九九七年七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61]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202页。
[62]《吴冷西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北京:新华社“革联”《倒海翻江》造反团,1967)。
[6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六月七日人民日报。
[6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65]《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1957)11页。
[66]吴祖光《“二流堂”奇冤大案》1991年3月19日 北京。
[67]《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12页。
[68]《争鸣》月刊(香港: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号43页。
[69]1958.4.6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110至111页。
[70]《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5页。这段话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删去了“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改成:“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37页。
[7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323页。
[72]《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3页。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作了修改,改成了“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见该书334页。
[73]1957.1毛泽东在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7页。此文未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74]同上,《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8页。
[75]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21页。后来这段话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改成了:“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再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见该书352页。
[76]1957.1毛泽东在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9页。
[77]同上。
[78]1957.1毛泽东在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10页。
[79]《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三期22页。
[80]同注[11],13页。
[81]1957.10.13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63页。
[82]1957.3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的讲话,戴晴《粱漱溟、王实味、储安平》(1989)194页。
[83]1957.3.17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林学院,1967)252页。
[84]1957.3.18毛泽东在山东济南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62页。
[85]1957.3.2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27、30页。
[86]《中国知识份子悲欢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225页。
[87]同上,227页。
[88]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1957.3.19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9∼1957.12)》[编者不明]158、159页。
[89]1957.10.13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63页。
[90]1958.1.28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上,93页。
[91]1958.3.25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191页。
[9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485页。
[93]1957.4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中讨论时的插话(整理),《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42至50页。
[94]1957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大学,1967年9月)126页。
[95]1993年9月30日美洲《世界日报》,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
[96]1957.3.19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9∼1957.12)》【编者不明】153页。
[97]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199页。
[98]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99]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206页。
[100]《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五期91页。
[101]1957.3.19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党员干部会议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林学院)288页。
[102]《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47页。章伯钧在中国民主同盟传达的稍不同:“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见《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一期20页。
[103]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47页。
[104]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550页。
[105]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井冈山》报(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106]1958年1月28、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138页。章伯钧,中国民盟副主席、国务院交通部长、罗隆基;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长。
[107]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108]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10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国青年报》。
[110]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111]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美洲《新闻自由导报》。
[112]《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阴谋》(编者不明,1957年7月)74至75页。
[113]王造时对记者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日报。
[114]1957.5.15人民日报,见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191页。
[115]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沈阳日报。
[1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117]《巢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一,朱元璋敕赐俞通源铁券文:“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者若犯死罪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
[118]1957.8.2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219-220页。
[119]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文汇报。
[120]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327页。
[121]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红旗战报》(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122]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123]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1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613页。
[12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4至427页。
[1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78页。
[1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614至615页。
[1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613页。
[129]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Thinkers Publishing Limited,2006)149-150页。
[1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89页。
[131]黄秋耘《风雨年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76页。
[132]《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一期74页。
[133]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323页。
[13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835页。
[135]《任仲夷反省历次政治运动》,原载于《南方周末》,见2002.5.26《中国事务》。
[136]1957年5月21日《广州日报》。
[137]《钢与渣》(北京:清华大学团委会,1958)第六期3至5页。
[138]参加彭真召集的谈话的清华大学团委书记阮铭一九九七年七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39]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202页。
[140]《吴冷西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北京:新华社“革联”《倒海翻江》造反团,1967)。
[141]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六月七日人民日报。
[142]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143]《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1957)11页。
[144]吴祖光《“二流堂”奇冤大案》1991年3月19日 北京。
[145]《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12页。
[146]《争鸣》月刊(香港: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四月号43页。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