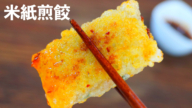去阿里山和日月潭,是我筹划已久的一次旅行。十月底,趁着瑞典学校放秋假,我独自踏上了赴台湾的云游之路。
1946 年11月,我的父亲作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的学生,曾到台湾地政局短期实习,考察了台湾多个县市。因此,我这次旅行不是一般的观光。除了要参加《瑞典森林散步》一书的新书发布会之外,流亡十六年未能回国探亲的我,还想在台湾寻找父亲六十年前的足迹,以宝岛的山水之美,慰藉我无以派遣的乡愁。
在幽静的阿里山忆起师涛
终于又闻到稻谷的清香了。在台南平原,我请司机停车,让我到久违了的稻田里,摘下一支稻穗作为纪念。出身乡村教师家庭的我,从小在湖南的稻田里长大,长期流亡在一个高科技工业化的冰雪北国。异域思乡的梦中,时常萦绕着水稻的香味。
台湾令我惊叹的,是它那奇特的热带水果,还有丰富别样的热带树种。车行阿里山上,我们穿越了热带林、暖带林和温带林。低海拔的田园风光,高海拔的森林山景,一切尽收眼底。下午,人们聚集于山顶的阿里山车站,欣赏邹族原住民的传统歌舞。之后,游客渐渐散去。我独自在山顶幽静的阶梯上坐下。
傍晚的云雾,从山下缓缓地升腾上来。千山万壑淹没在暮色和云雾之中,只留下这黛绿色的山顶和我。在“斜晖脉脉水悠悠”似的伤感与惆怅里,我还体验到一种“我与青山同在”的甜蜜感。带着惆怅与甜蜜,我走进山间一个小饭馆。
饭馆老板端上什锦火锅,还有一碟拌大蒜与醋吃的山猪肉。在北欧已经多年没有吃过火锅了,我兴致勃勃地给火锅拍照留念。突然,餐桌上的一张报纸吸引了我的眼光,那是10月30日的“苹果国际”,上面有一张我熟悉的照片——师涛,在他的眼镜下对我微笑。
正享受高山上的孤寂与野味的我,突然愣住了。自2004年起,这位记者政治犯就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他在湖南的牢狱里偶然读到我的小诗,写诗回应道:“你们,曾经给予过我多少温暖/ 我用这股珍贵的体温/ 驱散墙壁上厚重的寒气。”
我一时悲喜交集,泪水盈眶。喜的是雅虎和微软、Google终于共同签署了一项行为法规,承诺将保障全球网友的言论自由与隐私权,抗拒来自政府的侵犯。悲哀的是,为这项法规付出牺牲的师涛等人,至今仍在狱中忍受煎熬。
观玉山日出遇见大陆博士团
顶着几颗明亮的星星,我回到墙上画满山樱花的旅馆,伴着阿里山的林涛过夜。第二天凌晨,我便被人唤醒,坐森林火车去看玉山日出。人们都穿着厚厚的御寒衣服,在观景台耐心等待,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太阳在众人的欢呼中升起。
同在这山顶观日出的,至少有四个大陆观光团,一个是来台湾做教育访问交流的,一个是广东人的旅游团,还有在台湾大学里做短期交流的一个大陆法律博士班,一个大陆新闻博士班。独在异乡为异客,我听见大陆口音便感到亲切,很快就和他们交谈起来了。
一个大陆来的法律博士对我说,他觉得台湾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比较透明。一个新闻博士说,他们觉得台湾的新闻比较混乱,不够严肃。我说,尽管台湾新闻有很多八卦,但他们的记者可以揭露总统、批评政府,可以行使新闻监督的“第四权”,这是大陆媒体人享受不到的基本权利。
令我吃惊的是,大陆来的新闻博士不知道刘宾雁是谁,法律博士不知道师涛家属诉雅虎案,不知道胡佳因几篇文章被判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当代中国最著名的记者,被人从新闻史上轻轻抹去,当代最优秀的青年在受难,却不为他们的同代人所知。
阿里山明媚的晨光里,我禁不住黯然神伤。有时我曾想过,也许自己以后可以多写一些轻松的文学性文字,但这次遇见大陆博士团的经历,令我痛下决心:继续用文字来承担对历史以及受害者纪念的义务。就如索尔仁尼琴说:“没有纪念,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
在陈云林访台时举起红标语
日月潭曾是我父亲实习考察过的地方之一。傍晚和清晨,我从湖边旅馆的阳台上,眺望这个美丽的天然湖泊,遥想父亲当年。坐船游湖时,听导游介绍说,日月潭曾是蒋介石最爱的风景,附近凉亭与庙宇等不少景点,都留下蒋介石的遗迹。
父亲曾告诉过我,当年他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时,曾违背校长蒋介石的禁令,两次上街参加示威游行。其中一次是1947年,学生们抗议不是学者的蒋经国接任政大校长。那时的蒋介石似乎还有一点民主意识,虽然气得大发雷霆,但也没有处罚学生。到了共产党统治时期,父亲一类的国民党人,便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只求一条活路,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也许是继承了父亲反抗权贵的性格,回到台北后,正好碰上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访台,我便很自然地走上抗议的前沿。那是11月3日,我在街上一家做招牌的小店,订做了一副红布横幅,上面写着“释放王炳章胡佳陈光诚师涛等政治犯”。
当晚陈云林参加设于台北101大楼的晚宴,等我赶到时,已是下午五点半,绿营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等抗议人马,都已经聚集在大楼前。我把红标语藏在背包里,想要悄悄地混进101大楼去面见陈云林。但台湾警方在门前严阵以待,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当面向陈云林抗议。于是,我只好站在101大楼对面的市府路街口,当众展开红色横幅。
对我来说,这样的抗议是对狱中政治犯的一个道义声援,是向受难者及其亲属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一位台湾朋友评论说,茉莉这样的行为否定了陈云林来台的合法性,一个镇压本国人民的政权,怎么有资格代表中国?
新书发布会在抗议汽笛声中落幕
那天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在前去101大楼抗议前,我接受台湾名嘴胡忠信的采访,谈我的新书《瑞典森林散步》。采访结束后,胡忠信先生的助理——一位善解人意的小姐对我说:“陈云林来台湾了,按照你的性格,应该去抗议才是。”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正准备采访完后去取订做的标语,怎么就让这位小姐给猜着了?
也许那位助理小姐仔细读过我的书。我在书中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每当祖国发生了什么,流亡者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他们的态度,去充当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显然,那位小姐希望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接下来两天,我到国立政治大学、新竹中华大学和新竹教育学院,和大学生及博士们谈我的新书,谈瑞典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也谈“从欧洲经验看两岸关系”。正如此书的推荐人曾建元先生所说,遥远的瑞典对台湾人来说像是一团迷雾,他们对这个北欧小国充满了解的兴趣。
11月6日下午2时,允晨文化出版社假台大校友会馆,举办新书发表会。那天与会的,有台湾的文坛前辈、学界新秀、大学生和新闻界记者,还有旅台的西藏朋友和其他友人。
参加会议并发言的,有一位金发的瑞典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她是瑞典贸易委员会台北办事处的官员高夏琳。这位年轻的女外交官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向我表示祝贺。她还引用中国成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说茉莉这本书有中国人看瑞典的独特视角,令她爱不释手。台湾前笔会会长、诗人李敏勇先生在发言中谈及21世纪的流亡者,尤其是文化人流亡的问题,并表达他对台湾现状的忧虑。
我则以《放逐中的写作和精神回归》作为发言题目。这个题目来自李敏勇先生的一首小诗:“在秋天的山坡/ 通往天国的阶梯上/ 你的放逐/ 就是你的回归。”我谈到流亡者在异国吸取了新的文化营养,能够以写作为手段,在新的层次上实行精神的回归。
新书发布会场外,碰巧是民进党举行“围城”集合的济南路。抗议陈云林的队伍一片沸腾,人们不时齐吹汽笛,笛声响彻云霄。我在新书发布会结束之后,举起要求释放中国政治犯的红色横幅,再次走上台北街头。那里飘扬着青天白日旗,那是我父亲年轻时宣誓效忠过的旗帜。
--转自《争鸣》杂志200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