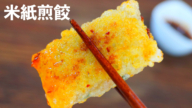【新唐人2019年05月03日讯】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当今中国是否还有新闻自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不简单。简单的是,几乎每天都有中共政府打压媒体,或是企业、媒体本身自我审查的消息传出来。不简单的是,中国的媒体环境纷繁复杂,要有一定深度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下番功夫。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通过审视中国调查报导的兴盛和衰亡的过程,从一个侧面为中国的新闻自由现状加上注解。
不到十年前,青岛人纪许光还是红极一时的中国调查记者。他2001年入职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迈入了他的记者生涯。此后十几年间,他先后在《民营经济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工作。他2006年涉足社会新闻,此后做了八年调查记者。
2012年,一篇名为《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文章在网上传开。正是纪许光在微博上实名举报了这位中共重庆官员包养二奶的情况,并以不雅视频截图为证。为此,举报人纪许光还上了央视新闻,描述他事后采访雷政富的情节。
“雷政富表现得非常着急,当然他那个时候还是在矢口否认的,但是这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有权对这个东西提出自己的意见。”
事件迅速发酵。此事曝光后不到三天,雷政富就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当年有人评价说,纪许光创造了中国网络反腐史上的最快纪录,号称“63小时秒杀一个正厅级干部”。

名记坐不住了
可就是这样一位曾经风生水起的媒体人,却越发感到力不从心。为了确保自身和家人的安全,纪许光于2014年携妻儿移民美国。今天看来,他觉得中国调查新闻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
“过去是尸横遍野,未来是一片迷茫,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大家不要再谈什么新闻理想了。”
中国媒体环境正在恶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近日,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推进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国际组织公布了2019年新闻自由指数。中国较去年又下跌了一位,在180个国家中位居倒数第四,不及越南和古巴。
2018年4月25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秘书长克里斯托弗·德鲁尔(Christophe Deloire)在巴黎展示“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
报告称,中共越来越趋近于当代版本的极权主义,外国记者越来越难在中国开展工作。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了多位前中国调查记者,了解这个行业的当前形势。虽然他们目前都没有继续全职从事调查报导,但一些记者仍在撰写调查类报导。
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舆论审查环境渐趋严峻,调查报导的选材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出于安全原因,部分受访人表示不便透露真实身份,本台使用化名替代。
调查报导一向被认为是新闻业中投入最多、风险最高的“硬骨头”。在中共官媒看来,调查报导是一个西方词汇,他们更喜欢把这样的文章称作“深度报导”,也就是业内俗称的“剥洋葱”。

丧钟为谁而鸣?
纪许光认为,中国调查新闻的空间已经几近枯竭了。现在是苟延残喘的阶段,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氧气可言了。如果说中共不想让你活的话,谁都活不了,这就是中国媒体的悲哀。
2014年,广电总局在换发记者证时,首次要求所有中国记者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以便他们“更有意识地保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016年,习近平在京召开舆论座谈会时更是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作为党政宣传阵地,这些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党媒“人民网”近日发布了一则首席调查记者的招聘启事。其职位要求的第一点便是中共党员,并要坚定“四个意识”、树牢“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而记者的专业素质却位居其次。
谈到中国媒体的里程碑事件,近年来引发国内外最大轰动的风波可能就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了。2013年1月3日,这家曾被外媒形容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的新年献词,在出版前被强行修改,而原本呼吁宪政的内容变成了对执政者的赞歌。
第二天,曾在这里工作的50多名新闻人联合发表公开信,要求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引咎辞职,而《南方周末》员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在其总部大楼外一度发生对峙。
“都说媒体是一个没落的行业,我觉得的确是的。目前,国内很多还在媒体的人会不断地给媒体唱赞歌,唱好调查报导,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媒体真的很不幸。可以说在2013年后,它已经面目全非了。”
濒临灭绝的物种
如果说不少媒体人感到中国调查新闻正在发生质变,那么学界证明了它也在经历空前的量变。
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2017年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调查新闻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经过双重核实,他核定中国仅剩175名调查记者。与2011年首次调查结果相比,人数几乎被腰斩。中国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国内持证记者人数在2017年超过了22.8万人。这意味着每1300位中国记者中,平均只有一位是调查记者。
他还表示,调查新闻行业近年来承受了多重压力。一方面,微博微信等社媒的兴起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文化权威,导致调查新闻面临着社会影响力衰落的考验。由于发行量下滑,这些传统媒体的广告费较往年大幅下降。为了节约成本,一些都市报裁减甚至撤销了调查新闻部门(业内普遍称之为“深度报导部”)。
另一方面,随着党政宣传报导力度的增强,媒体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为了维稳,对敏感社会问题加强了行政管控,进一步压缩了报导空间。
我还能报导什么?
现中国某一线杂志记者赵蕾2016年曾在《新京报》调查组实习过几个月,此后她还在报社的突发组和深度人物组工作过,直到上个月跳槽。回顾在《新京报》的三年,赵蕾坦言,单位的报导尺度明显缩水。
“我记得2016年年底前,其实报社的尺度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北京很多负面的调查报导,比如说哪里采矿死了人,大家还是可以报导的。但是2017年之后,就不太乐观了。然后2018年,报导限制就更明显了。”
她举例说,继2017年#MeToo(“我也是”)反性侵运动在美国好莱坞爆发后,中国“米兔”运动仍方兴未艾。但当《新京报》前一阵儿想就此做些剖析时,她们就接到了主管部门的通知。
“我们就只是碰了一下,然后只要碰了,禁令就会来得非常快,后来我们就干脆不碰了。所以米兔运动我们报导得非常少。”
赵蕾表示,她当年在调查组实习时组内的六七位全职记者目前都已离职,而接替他们的基本都是“90后”。她说,老一辈调查记者普遍都有自己的成名作,也相对更受人尊重。在中国调查新闻的黄金时代,他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
怀念最好的时代
业界普遍认为,广州《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2003年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标志着中国调查报导步入了黄金时代。这篇报导记载了在广州工作的外来务工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送至收容站后遭殴打身亡的事件。此事引发了中国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热烈讨论,并最终促成当局废除这项制度。
此后几年,中国调查新闻渐入巅峰。期间,多位记者因报导重大社会事件,他们的名字也与这些作品一道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其中的一些代表作包括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发表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重启尘封十多年的聂树斌案,显示他并不是本案真凶。
2008年,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文章,完成了一起特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首次曝光;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揭露了当地的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
当中,王克勤由于长期从事调查报导,发表了无数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推动政策法规变革的文章,被业界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即便已身经百战,他还是没能逃脱行业的变迁。2012年底,随着他后来任职的《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他淡出了新闻圈。作为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发起人,他近年来致力于推动中国数百万尘肺病农民的救助工作。
本台记者联系到了王克勤,但他表示,自己离开老本行已有多年,不便置评。
“我离开本行的时间很久了,也不便说什么了。”
不光是他,很多前些年声名大噪的调查记者也已告别了本职工作。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揭发三鹿“毒奶粉”事件的简光洲在2012年8月离职。那一年,他在微博中说:“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目前,简光洲在上海一家公关公司做总经理兼合伙人。
而对聂树斌案提出质疑的范友峰也在报导发表后被辞职,而这起冤案最终在2016年得到平反。范友峰于2008年淡出新闻一线,从事广告经营,目前担任《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经理。

一切都只是海市蜃楼?
现居美国的前调查记者纪许光对中国调查新闻曾经的辉煌不屑一顾。他坦言,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渐渐意识到,这些调查记者其实都是中国政府的棋子,他们的生与死终究由不得自己。
“中国媒体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博弈的空间。共产党之所以让它活着,是因为党内有一股力量需要它。当不需要它的时候、当党的声音要趋于一致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全都得死。”
说到触碰当局红线的新闻人,前调查记者刘虎或许就是一个例子。2013年,时任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涉嫌渎职犯罪,被北京警方在其重庆家中以“造谣”罪名刑事拘留,直到近一年后才得以取保候审。
43岁的刘虎可谓是见证了中国调查新闻的大起大落。他2004年入职《重庆晨报》做机动记者,2008年来到《成都商报》作全国性报导。出狱后不久,他就与武汉《长江商报》签约,继续他的本职工作,并在此期间写下了贵州茅台虚假广告的调查报导。但就在这家报社因报导一系列敏感事件被勒令整顿后,刘虎于2015年离开纸媒,成为了自由媒体人。
刘虎的记者十年与这个行业一同沉浮,打磨了他犀利的观点。他对本台记者表示,虽然中国调查新闻的下坡路看似也与市场动荡有关,但这到头来还是政治环境的产物。
“市场形势也是政治因素引起的。中国的舆论管制导致媒体不能报导一些事情。这导致了在市场化的媒体环境中,就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这造成了读者的流失和订阅量的下降,降低了对广告主的吸引力。这样的话,媒体的收入下降,很多媒体不得不缩减版面,有的直接就停刊了。”
人都需要好好生活
此外,一些年轻记者对调查新闻还存在一个心结,那就是薪水太低。北京某都市报前调查记者陈晓(化名)对本台表示,她们承受的压力可以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女的当男的使,男的当牲口使。”
她表示,即便如此,很多都市报调查记者的基本工资都很低,而她们主要靠拿稿费过活。但由于调查报导通常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她感觉付出和收获之间的反差太大。
“我原来的同事和现在(在调查组工作)的同事做调查新闻,其实心里面并没有想着要赚钱,我们都还是希望能做出一些东西、起到一些作用。但如果做的时间特别长,而经济方面一直都赶不上你的付出的话,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落差吧。”
前《新京报》调查组实习生赵蕾表示,据她从几位业内人士了解到的情况,一篇四五千字的普通调查报导的稿费大概在6000到8000元不等,而特别出色的报导的稿费最高可能也不过一两万元。
陈晓说,自从她2015年底入职到去年调入报社的另一个部门,此前与她一同工作的调查记者都已离开了原岗位,他们中有的做起了企业公关,有的回老家投靠了当地媒体,有的和她一样,进了报社的其他部门。她说,很多资历丰富的调查记者如今都另谋高就了,而这其中不乏现实原因。
“有些人做了小领导,然后又去做公关,赚钱去了。有些人自主创业,做个自媒体,可能有更好的发展,然后就不会坚持做调查新闻了。调查新闻确实很苦很累,很耗时间。有时候你调查一件事,可能跟踪好久都没能作出报导。”
寻求心灵救赎
在与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短信交流中,前调查记者纪许光坦言,移民美国五年来,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不该再延续以往的“自我审查”了。但与此同时,作为调查记者,他理应身处最黑暗的新闻一线,而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这也是他决定潜心学佛的重要原因。
“我的职业让我看到了社会太多太多的阴暗面和人性之恶。但是佛教又被称为圆教,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心灵上的良好慰藉。”
纪许光痛斥中国如今的政治风向,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那个当今皇上,掉头飙车!千古罪人!!”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责任编辑: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