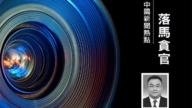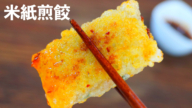一朝成罪犯 永远是罪犯
任何认为指控有可能不成立或者受审者有可能被宣判无罪的想法,在该系统中都没有空间。在中国,人们不是因有罪而被捕,而是因被捕而有罪。所有逮捕都是由警方进行的。警方是由共产党领导、受毛泽东掌控的“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质疑一个人被捕的原因,无异于反对毛主席,从而揭示出一个人真的是“反革命分子”。按照同样的推理过程,任何监狱看守不被人服从,都可以直接大喊:“什么!你胆敢违抗人民政府?”承认罪行并完全服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自我苛评(Self-castigation)是牢房里的规则:“你是一名反革命分子。我们所有人都是。否则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根据该系统的癫狂逻辑,被告必须自己为自己的被捕提供理由。“告诉我们,你为何在这里”通常是指导员问新囚犯的第一个问题。囚犯必须起草自己将面临的指控,包括对量刑的建议。他们也被要求提供连续的供词(一出现严重问题,他们就必须从头重新开始)。这有时需要几个月时间,且有时长达数百页,详述了人们整整几十年的生活。审讯本身长时间进行,有些长达3,000小时。正如人们所说的,党有充足的时间。审讯人员经常使用的手段有剥夺睡眠(许多审讯在夜间进行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威胁要予以极端的惩罚甚至处决,或让囚犯对酷刑室(后来据称是一座“博物馆”)进行令人恐怖的参观。
上海一座监狱的前囚犯郑念(Nien Cheng)回忆说:
我从监狱医院回来的当天,值班看守就给我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她说:“继续写你的交代!审讯员正等着呢。”
我拿起审讯员给我的那叠纸,看到和1966年冬要我写自传时给我的纸不一样。那次是空白纸。这次,在纸的第一页上印有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在印有“最高指示”的标题下, 是一个用红线划出的方框,里面印着:“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纸的底端通常为囚犯签名的地方,印有“罪犯签名”的字样。
我的直接反应是对“罪犯”这个侮辱性词语很是恼火,决心不在其后签名。不过,想了几分钟后,我设了一计要利用这种情况……
在毛这句印刷的语录下方,我也划了个方框,也在其上方写了“最高指示”,并在方框内写上毛的另一段语录。它并未出现在红宝书中,但我记得是来自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这段语录称,“哪里有反革命,我们必定进行镇压;我们做得不对,就立即改正。”……
我把那张纸交给值班看守。当天下午,我就被叫去受审问。
除了那名士兵外,屋里还是原班人马。个个脸色阴郁。早在我决定与他们争辩我无罪之时,我就对他们这种神情有所准备了。未等审讯人员示意,我便立即向毛泽东的肖像鞠了躬。审讯员选给我阅读的语录是:“我们必须实行全面的专政,来镇压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以及那些代表地主和国民党反动集团利益的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我写的那张纸到了审问员面前。我坐定后,他一边瞪着我一边猛敲桌子,然后又猛敲桌子,大声说:“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他指了指那张纸。“你以为我们在和你做游戏吗?”
我沉默不语。
“你的态度不端正”,那老师傅说。
“你要不端正态度,就永远别想离开这里”,那年轻工人说。
未及我开口,审问员便把我写的那份交代扔到地上,页面散落开来。他站起来说道:“回牢房重新写!”
一名看守出现在门口,喝道:“出来!”
身体暴力本身相当罕见,至少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文化大革命之间。任何类似酷刑的手段,如殴打甚至侮辱,都被严格禁止,囚犯们知道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受到了虐待,就有一些获得赔偿的小小希望。因此,唯一真正的暴力非常不易察觉,或存在于“批斗会”中,会上允许其他囚犯对受害者进行殴打;或存在于牢房监禁中,牢房无供暖、不通风,小到不可能伸直四肢。在那里,囚犯被永久性地戴上手铐或用锁链拴住,经常双手反背于背后,结果保证卫生和吃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惩罚持续8天以上,这些牢房里的囚犯通常就会死亡。永久性地戴上过紧的手铐,是最常见的一种准酷刑,导致双手迅速肿胀、难以忍受的疼痛以及往往不可逆转的疤痕。
将那些特殊的手铐紧紧地戴在囚犯的手腕上,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监狱系统常用的一种折磨方式。有时囚犯的脚踝上还会套上额外的锁链。在其它时候,囚犯可能被戴上镣铐,然后其手铐被绑在窗栅上,这样他就无法离开窗户去吃、喝或上厕所。目的是侮辱人的人格,以摧毁其意志……由于人民政府声称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酷刑,官员们索性称这类手段为“惩罚”或“劝说”。
这些措施的官方目的是获得一份供状(其本身具有举证力量),以及显示囚犯诚意并证明警方指控是很有根据的多份揭发书。规则是三次揭发就证实逮捕是对的,因此链条无休止地延伸下去。除极少数情况外,警方使用的手法与各地警方所使用的相同:突出矛盾,假装已经知道一切,并把一份供词与其它供词或揭发相比较。无论是以暴力逼迫的还是自发的(大多数城市的街头都有一个特殊的“举报箱”),揭发一般来说很多,以至于很难掩盖一个人的过去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任何事情。正是看了揭发自己的信件,最终打破了帕斯夸里尼的抵抗:“这是一次令人恐惧的揭发。那数百个页面上,有同事、朋友和我只遇到过一两次的各种人手写的检举材料……我不假思索就信任的多少人都背叛了我!”郑念于1973年获释、未做任何坦白。这一点颇不寻常,部分是由于其非凡的性格力量,部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后警方做法上发生变化。在之后的多年里,她周围满是亲戚、朋友、学生和佣人;他们所有人都把她举报给了安全力量。其中一些人甚至也承认这一点,声称他们在此事上别无选择。
当案件最终准备就绪时,囚犯犯罪的“真实故事”就以囚犯和法官联合制作的形式上演,其措辞完全颠覆事实。罪行“必须产生了一些真正的影响”(如果法官和囚犯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一点,它就更有用,如果其他人也牵涉其中,那就很有帮助了),但它完全是以偏执狂的方式重塑,如同一些激进而绝望的政治反对派的不断表达一样。因此,在国外的一封信中提到大跃进期间上海口粮略有下降这一简单行为,就成为证明一个人是特务的官方证据,尽管这些数据已在官方报刊上发表且为城里所有外国人所熟知。
通常的结果是放弃人格,正如帕斯夸里尼所证实的:
囚犯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丧失自信。多年来,毛的警察已经将他们的审讯方法改进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要对抗任何人来顶住他们的压力,无论他是否是中国人。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让你发明不存在的罪行,不如说是让你承认你的日常生活糜烂、罪恶且值得惩罚,像你曾经过的那样,因为它不符合警方关于生活应当怎样过的概念。他们成功的基础是绝望──囚犯认为其完全、无望地、永远地受到狱卒的摆布。他没有做任何辩护,因为他被捕就是他有罪的确凿和毋庸置疑的证据。(在多年的牢狱生涯中,我知道有这样一名男子:他实际上是被误抓的──真有其名,但不是此人。几个月后,他供认了对方的所有罪行。当发现错误时,监狱当局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劝回家。他觉得自己对自己交代的罪行太有罪恶感了。)这名囚犯没有受审,只经过一个精心排练的仪式,或许持续半个小时,没有咨询律师,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诉。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