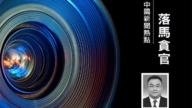长期以来,西方有一个颇受推崇的传说:红卫兵只不过是1968年法国革命者的一个稍微更狂热的版本。四人帮倒台之后,一种说法在中国流传:红卫兵是一群政治投机者的地下法西斯主义帮手。但这种传奇式的说法远非事实真相。现实情况则大不相同:“造反派”认为自己是好的毛派共产党人,未受任何民主或自由理想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正是如此。在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整个实验实际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但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共同代表了一个奇怪的另类共产党,此时真正的“共产党”因其核心的分裂而瘫痪。他们准备为毛献出自己的生命,虽然他们与林彪和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也有着强烈的个人和意识形态联系,但他们实际上只是一种替代品,因为他们反对反毛的省市当局。他们当然也是北京宫廷权斗的一支补充力量。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的冲天干劲,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在掌权的短暂时期内,他们完全一无所获,也未能对业已实施的极权主义结构做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红卫兵经常佯称,他们的目的是效仿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但他们组织的选举从来都不是自由或公开的。所有决定都是由小型的、自我任命的团体做出的,任何变化都只是该运动内部及它们控制下的行政机构内部斗争的结果。不时有小型的、个人的胜利,工厂工人的一些社会需求得到满足,但这些成绩只是让1968年回归常态更加艰难。
红卫兵以诸多不同的方式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关联。1966年6月和7月,由刘少奇团队派入主要教育机构的工作组和依靠他们的各省级团体,为教授们建立了首批“黑窝点”,并为第一批红卫兵组织提供了动力。尽管它们在8月初正式停止运行,但作为毛的中央委员会工作组的一部分,它们有时仍在各地方组织中产生持久影响。无论如何,它们是教育系统中对教师和干部系统性诉诸于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它们为破“四旧”运动开辟了道路。那场运动虽然得到了地方当局的支持,但主要是警方的事。警方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收集证据并没收财产。1978年,郑念重新找回了她的大量瓷器收藏品,感到又惊又喜。这些收藏品是20年前在这样的暴力环境下被没收的。当时,那些参加过以前运动的人以及一些中层干部被当作替罪羊,以保护曾一直在真正指挥行动的人。
这场运动延伸到工厂。与此同时,毛越来越意识到,他的目标──消灭所有政治对手──正在脱离他的掌控。这一切导致造反派与省市当局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但地方当局总是非常清楚如何策划大规模示威。这些示威活动很难与更靠近毛泽东路线的造反派的示威区分开来。另一方面,造反派在地方上更加独立,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是一种救赎,与中央文革小组所变成的“超级中央委员会”保持一致。康生在其中扮演着谨慎而重要的角色。专门的团队与北京保持密切联系(在早期,这些团队通常由来自首都的学生组成)。他们提出建议和黑名单(包括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成员的名字),等待结果和证据,并用珍贵的“无罪标签”奖励其盟友们。这些标签被用作躲避解放军的一种护身符。造反派正如其对手一样依赖国家机器,但是以不同的方式。所有团体都在镇压问题上团结一致,这是与西方革命传统的一个巨大差异。如果劳改营在任何时候遭到批评(很少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它们管理松弛:例如,郑念回忆起新毛派监狱看守是多么残忍和不人道。华林森(Hua Linsham)是一名极左造反派,且公开反对解放军。他在一家制造武器的监狱工厂工作;然而“在我们待在那儿的整个期间,囚犯们待在他们的牢房里,我们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红卫兵用绑架作为其镇压军械库中必要的武器。他们在每间学校、政府办公室和工厂里都有自己的监控网络。在这些“牛棚”(首选的委婉说法是“学习班”)里,人们受到监禁、审讯和不停的折磨,其过程小心翼翼,充满想像力。Ling回忆起其学校里的一个非正式的“心理研究小组”:“在小组会议上,我们避免提及酷刑,但我们认为酷刑是一种艺术……我们甚至认为我们的研究不充分……有很多方法我们无法测试。”杭州一个“激进”的民兵组织,主要由自身遭受过迫害的“黑类”组成,通常在任何时候,其3个“调查中心”都有1,000人。它控告23人诽谤其领导人翁森鹤;其工作人员每工作一天,就休息三天,并免费用餐。在前红卫兵所做的所有陈述中,对镇压行为的描述占据核心地位。有无数关于敌人的故事。他们被打倒在地、四处游街、受到羞辱,有时被杀,看似没有来自任何一方的反对。文革时期的显着标志还有再次囚禁前在押人员、再次应用以前去除的“右派”标签、系统性地逮捕外国人或曾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还有新的恶行,例如女儿有义务服完亡父剩余的刑期。“民政管理机构遭受严重打击,劳改管理机构受到的打击则要小得多。或许这一代人是监禁者而不是造反派的一代。”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甚至是关注打造新理论的激进造反派组织,例如湖南的“省无联”组织,都无法摆脱极其有限的毛主义框架。毛的思想总是那么含糊,而且他的言辞如此矛盾,以至于它们可以转变成几乎任何意思:保守派和造反派都有他们的引文库──有时引语相同,解读却不相同。文革期间的中国是个奇怪的地方,一名乞丐可以引用毛关于互助的言论来证明偷窃是合理的,地下经济中一名偷砖的工人可以毫无顾忌,因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总有一个确凿的核心思想:暴力的神圣化、阶级斗争的激进本质及其政治涵义。对于遵循正确路线的人来说,任何事都是允许的。甚至造反派也无法与官方宣传保持距离;他们的文本密切模仿党的官方语言。他们不仅向群众,而且向自己的同志肆无忌惮地撒谎。
拥护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等级制度,进一步成为一种共识,这或许是文革最具戏剧性的效果。情况本来可能大不相同。为加快进程,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将其组织的大门向“黑类”打开。他们抢着加入。由于中国知识分子45%的子女入读了广州的学校,南方注册的学生人数高得不成比例。干部的子女和正式被认定为工人的人的子女,构成了南方大都市保守派的82%。受无公认地位的工人的支持所推动,造反派成为政治干部的天敌,而保守派则集中精力攻击“黑类”。造反派的计划包括消除社会政治分化,这使他们有望摆脱自己地位低劣的耻辱。因此,他们发起了一场针对保守派和“黑类”的镇压运动,希望这些打击不会降临到自己的亲戚身上。更糟糕的是,为了自己,他们接受了北京红卫兵提出的阶级遗传性的新概念。这些红卫兵大多是干部和士兵的子女。
例如,这一概念在一首引人注目的进行曲中得到了表达: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革命,就跟我走。 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 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们会逮到你! 杀!杀!杀!
一个“出身好”的人评论道:“我们是天生的红类!我们的红来自我们母亲的身体。而且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你们是天生的黑类!对此,你们还能做什么呢?”类别的种族化是毁灭性的。皮带在手,翟振华摆出准备辱骂的姿势,迫使其阶级中半数“黑”类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研究毛上:“如果他们要拯救自己,他们必须先学会为其糟透的家庭出身而感到羞耻,并憎恶其父母。”当然,他们是可以加入红卫兵的。红卫兵在北京的火车站巡逻,痛打任何出身不对的红卫兵,并把其遣送回家。在各省,人们往往较为宽容,那里“黑类”有时的确担任职务,但优势总是归于“出身好”的人。有一个绰号为“小猪”(Piggy)的女生,Ling回忆说:“小猪的阶级背景──一个重要资格,非常好:她来自一个石匠家庭,经常吹嘘她家三代以来头顶从未有过屋顶。”在任何口角中,阶级牌总是被打出来,且总是赢。华林森是一名非常激进的造反派,曾经被一些相当保守的红卫兵扔下火车:“今天,我仍旧感觉到,当时他们发现我的实际存在是多么令人反感和肮脏……我突然觉得我相当令人厌恶。”在示威中,父母为红五类(党员干部、军官、工人、贫农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一直起着主导作用。隔离制令整个社会分裂。在1973年的一个居委会会议上,郑念错误地与无产阶级一起坐了下来。“仿佛他们受过电击一样。最接近我的两名工人立刻将他们的凳子从我身边移开,结果我就孤立地坐在拥挤的房间里。”然后她走过去加入一群妇女、“受谴责的资产阶级成员和知识分子──文革弃儿”。她明确指出,实施这种隔离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党。(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