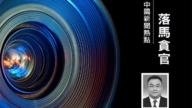1974年12月25日,葡萄牙军官在里斯本建立多党制民主政体时,将莫桑比克的命运托付给一个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tação do Moçambique),即Frelimo。该阵线在人类学博士爱德华多.孟德兰(Eduardo Chivambo Mondlane)的领导下于1962年6月成立。它设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军事支持。与安哥拉不同,Frelimo在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前夕,设法给殖民部队造成了严重问题。部队中大多数人是非洲血统。由于Frelimo已赢得很大一部分民族主义知识精英的支持,因此该阵线反映了知识分子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到1974年,马列主义显然在Frelimo的领导层中占了上风。在1968年Frelimo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正如萨莫拉.马谢尔根据中国的“解放区”概念所述,反帝斗争逐渐采取了孟德兰在1969年去世前不久所提出的形式:“我今天的结论是,Frelimo比以往更加社会主义、更具革命性和更进步,我们的路线现在坚定地面向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了解释这一演变,他补充说:“基于莫桑比克当前的生活条件,我们的敌人让我们别无选择。”
独立后,这个“敌人”似乎立即给了该国新统治者一些喘息的机会。在新体制中起主导作用的白人、混血和印度裔同化民发起了对该国的重大重组。他们相信,莫桑比克本质上是个农村,只能以党国的形式存在,因此试图通过一个叫做“村有化”的过程来控制该国。这项政策最早是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解放区”实施的,在那里已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Frelimo决定将其系统性地扩展到全境。所有农民(占人口的80%)被要求抛弃他们传统的家园,并在新的村庄重组。出于最初的独立热情,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回应,创建了集体农场,有时还合作建造公共建筑,尽管他们通常拒绝居住,并很快放弃了公共田地。从理论上说,该国似乎是通过共产主义单元的网络,处于分级管理的精心控制之下。
1977年,Frelimo领导人公开宣布效忠于布尔什维克理想,要求扩大集体化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苏联阵营国家签署了各种条约。这些国家提供武器和军事教官,以换取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的罗得西亚民族主义者的密切支持。
莫桑比克忙于同东方集团(Eastern Bloc)(很快开始掌控该国)签署协议时,以伊恩.史密斯(Ian Smith)为首的罗得西亚白人,通过支持在农村开始出现的抵抗运动,试图进行报复。在阿方索.德拉卡马(Alfonso Dhlakama)的领导下,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Resistência Nacional Moçambicana,即Renamo)得益于罗得西亚特工机构的支持,直到1980年津巴布韦实现独立。那时南非政府接管了对Renamo提供后勤支持的责任。令众多观察者惊讶的是,乡村人口团结起来支持该抵抗运动,尽管Renamo的手段很野蛮,甚至让罗得西亚人都感到恐惧。Renamo的一些支持者是逃离国家人民安全局(Serviço Nacional de Segurança Popular, SNASP)“再教育营”的人。这些“再教育营”在1975年以后变得无所不在。SNASP曾经以为,即使无法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至少也可以控制他们。控制民众对双方都至关重要。鲜有现场进行的研究证实双方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之规模和严重性。总体而言,Renamo的行为远不如Frelimo犯下的国家暴力那样系统化,而Renamo所获得的支持恰好表明该政权已变得多么可恨。以斗争为名,Frelimo为自己的行动正名,声称它反对部落主义、陈旧过时的宗教习俗以及对血统和祖传封地的深厚信仰。独立伊始,该阵线就拒绝了这些传统,将其贬损为“封建主义”。
甚至在马普托(Maputo)当局意识到Renamo带来的危险程度之前,SNASP的特权就已大大扩展。SNASP成立于1975年,负责逮捕或拘留任何涉嫌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威胁国家安全的人。SNASP理应遵循正常的司法程序并自行进行起诉,但它也有权直接将人送往“再教育营”。《刑法》第115条为这一做法提供了便利。该条款取消了在押人员的人身保护权(尽管在萨拉查政权下该权利的大小程度相当有限)。抵抗组织的首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1977年,针对的是位于萨库泽(Sacuze)的再教育营。由萨莫拉.马谢尔定期倡导的守法运动(ofensivas pela legalidade)并没有取消SNASP的特权。相反,这些运动旨在让法律符合现状。这就是1979年2月28日第2/79号法律背后的逻辑。该法律涉及危害人民国家安全罪和危害人民国家罪。该法律还重新引入了1867年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均已废除的死刑。不过,死刑并没有被系统地使用,除了用于消灭Frelimo异见者外。例如,拉扎罗.恩卡万达梅(Lazaro Nkavandame)、若阿纳.西迈奥(Joana Simaiao)和乌里亚.西芒戈(Uria Simango)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1983年在被拘留期间受到清算,其死亡一直被保密,直到该党的马列主义时期正式终结。1983年,马普托大学的爱德华多.孟德兰(Eduardo Mondlane)法学院关闭。这也许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根据政府的法律报告,该机构的职能不是准备好律师来捍卫民众的利益,而是培训剥削他们的人。
知识分子很快就对该运动不再抱有幻想,尽管他们确实对一个在理论上保护他们利益的组织──莫桑比克作家协会(Associação dos Escritores Moçambicanos)深表赞同。他们还与中情局、克格勃和SNASP本身之类的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较为罕见的是像诗人豪尔赫.维埃加斯(Jorge Viegas)这样的人,因为政见不同而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并流亡。
遵循苏联体制初期的逻辑,政治路线的强硬化与经济的开放双管齐下。投资总是来自国外,在Frelimo统治下继续这样,这一点恰好适合一个被苏联禁止进入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国家。1983年Frelimo第四次党代会之后,该组织将注意力转向农村人口,终止了已造成如此灾难性后果的集体化政策。在一次典型的谴责中,萨莫拉.马谢尔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往往会忘记我们的国家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我们不停地谈论工人阶级,并将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抛诸脑后。”每次政府民兵又烧毁一个干草堆以确保村有化配额时,都会增加对Renamo的支持。对传统农业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连同消费品对食品极不稳定的比价,已导致食品供应出现严重问题。
政府和Renamo似乎都没有系统地使用过饥饿武器。但是,在从双方有争议的地区转移人口时,控制食品供应成为Frelimo至关重要的工具。将农民与他们的土地分开也是一项灾难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该国的粮食短缺。据人权观察组织说,1975至1985年间,粮食短缺比武装暴力导致了更多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认同这一观点。该机构估计,在此期间有60万人死于饥饿,这一生命损失可与埃塞俄比亚饥荒所造成的相提并论。国际援助是帮助受影响人口生存的主要因素。1987年1月,美国驻马普托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多达350万莫桑比克人受到饥饿的威胁,促使华盛顿和一些国际组织立即作出反应。尽管作出了这一努力,但最无防备的地区仍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饥荒之害,饥荒的规模从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仅在门巴(Memba)地区,人道主义组织就报告说,1989年春季,有8,000人死于饥饿。市场力量很快在获得国外支持的地区占了上风。这就是从1991年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一份报告中所汲取的教训之一。该报告显示,只有25%的粮食援助按商定的汇率出售,而其它75%则留在了当局手中,当局在进行了通常的偷窃之后,在黑市上将其出售。萨莫拉.马谢尔及其伙伴如此热衷于培养的莫桑比克“新人”,暴露出自己是每个人内心妥协的极具病理性的产物,表现形式为羞辱、欺骗和精神分裂症的疯狂。个体想生存下去,必须把自己分成两半,过着双面人的生活,一种隐藏的、真实的生活和一种虚假的公开的生活,第二种保护第一种。“他必须不断地撒谎,以保有自己的那一点真相。”
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突然崩溃促使人们意识到,这些政权是多么脆弱、公民社会可能是多么具有反抗性。即使在这里所涵盖的15年中,非洲共产主义被公开描述为“现代政治合法化”(modern political legitimation)或已对该地区的大学讲师造成了痛苦的后果,但这种看法确有一定的解释力。非洲共产主义试验的短暂性,加上认为非洲本身注定要遭受暴力的主导性看法,可以在开始时提供一个轮廓,但存在令该项目内在细节模糊化的风险。为了抵制这种认知的诱惑,我们或许应该采纳一项相反的看法。正如阿希尔.姆边贝(Achille Mbembe)所说的,尽管可能难以看到这些马列主义国家本身暴力的特定性质,但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之所以发生了饥荒和对平民的屠杀,是因为这些非洲国家“在被西方列强殖民并引向独立后,选择了以苏联式政权为模式”。这种模式确保了促进民主化的努力将几乎无助于改变大多数非洲国家深刻的列宁主义性质。(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