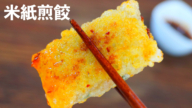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9月09日讯】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一位有着非同寻常经历的女士,她是中美混血儿,出生在纽约。不到2岁,被带回中国,这一待就是30年。她成长的岁月正遇上文革,历经无数磨难,而她冲出中共铁幕回到美国的经历,同样惊心动魄。她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后,滞留中国的美国人回到美国的第一人。回到美国12年后,1990年她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折射》,自此开启了笔耕生涯。
她迄今已经出版了50多本书,并荣获了2020美国总统国家与社会贡献奖。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作家韩秀来跟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结婚后有时间 开始考虑写书
主持人:所以您回美国的时候是1978年嘛,那个时候是美中建交的前一年,然后您是1990年出版《折射》这本书的,中间过去了12年。那您是什么时候动念要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书,还是说您一直都在想这么做?
韩秀:没有,我念书的时候我的数理化特别好,我非常想做一个造船工程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做一个作家。那么我回到美国以后呢,你看过那本《多余的人》你就知道了,就是齐邦媛教授说的,我在华盛顿就成了香饽饽了,所有的人都扑过来说,你告诉我们这个,你告诉我们那个,包括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而且我在美国外交学院教书,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那么我在那儿教书,不但在那儿教书,而且晚上我还在Johns Hopkins(约翰‧霍普金斯)兼课,而且我还拚命念英文,我忙死了,真是忙得不得了,根本谈不到写作这件事情。
直到了1982年,我跟Jeff结婚,忽然我就有时间了,对不对?我跟他结婚,而且我得跟着他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不能把外交学院放在肩膀上,我也不能把Johns Hopkins背在背上,对不对?我必须要离开,我得做点什么,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我可以不用退休,可以一直做下去呢?写作。那个时候我的身体非常不好,背痛,我刚才讲到背痛就是这个痛,这个痛,痛到我简直是连鞋子都穿不上。
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写《折射》,我怎么个写法,我能活到我写完吗?很难说,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故事,就像一串珍珠一样,而且很多都是别人的故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出来,谁也不会知道了。在新疆发生的事情、在山西发生的事情、文革的事情,如果我不写的话,那不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所以我就尽可能地写,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实际上我们外交学院的这个外交官们,他们学中文的,一年的学习在华盛顿,一年的学习在台北阳明山上,然后才派到这些讲华语的地区去。那么Jeff的工作呢是这样,他在华盛顿念了一年,在台北念一年,然后派往北京美国大使馆。那是1983年的事情,所以1982年到1983年,我有这一年的时间在台北,在阳明山上。
在台湾大学学中国三十年代文艺思潮 在北京写书
在阳明山上,那外交那儿也有外交学院,他们就跟我说了,那你就来教书了,我说我到了台北我还要教书吗?我去念书好了,我家的隔壁就是文化大学,所以我就跑到文化大学去选了一年的课,选的正好是李超宗教授的课,谈的是中国三十年代文艺思潮。
我们这一接触,这位教授真的是对我好得不得了。而且好奇怪的那年轻的孩子们后边忽然坐了一个外国人,然后就讲一口京片子,然后这个一堆故事。所以他就把台北《联合报》的痖弦先生,以及台北的重要的作家们全都介绍我认识。所以我到1983年到了北京以后,写短篇小说都是通过外交邮袋直接寄到《联合报》。那个时候这些小说就发表出来了。
这个发表之前,我还去请教了美国的律师,我说我人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然后外交邮袋送稿件到台湾,我这同样的一个中文名字合适吗?那个律师说你得有个笔名比较像话,所以韩秀这个笔名就出现了,所以韩秀就在《联合报》写小说,而且写那个小说都是关于北京、关于中国、关于种种的黑暗,真是历历在目啊。
啊!这个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就有人问我说,嘿!Teresa,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叫韩秀的人啊?他在《联合报》上写小说,他可对咱们这点事儿门清,你认识不认识这人?我说没听说过。三年以后,我们告别北京,Jeff派驻联合国,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使馆的工作。
我们也不是从首都机场,我们还是坐火车到香港,从香港飞。离任的时候,那个作家协会的人在火车站送我。再见!韩秀。
主持人:人家也门儿清。
韩秀:最后才门儿清,太晚了吧,对不对?我这事儿是跟他们这不管什么事儿,我都比他们快半拍。你别快一拍,快一拍,太快也不行,你也不能慢了,慢了你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快半拍正好。
从炼狱出来的人 在新疆被砸晕三天
主持人:对。我看您书中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就说自己是从炼狱出来的人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个在新疆被一枪托的砸晕三天,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不管在山西、在新疆,在成长过程中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还有包括这个这种在新疆去搬死人……
韩秀:对,那个那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主持人:对,就说就是您写这个书的时候,您就是重温或者面对那些年的经历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心情?您觉得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这种体制、这种制度对人最大的摧残是什么?
韩秀:哎!这个中国这个体制,它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的。它希望所有的人都俯首称臣,希望所有的人都变成他们的工具。如果你不肯,它就要从思想上改造你,它改造的办法是把你送到比方说监狱、比方说劳改队、比方说劳改农场,比方说,这种各种各样的。但是如果你还是不肯接受的话,它要你在灵魂上屈服于它,但是如果你不肯,它就从肉体上消灭你。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那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会问,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怎么活着回来呢?那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地方嘛,对不对?你居然能活着回来,你看他这反应多彻底,多明白,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但是如果要是你不但在灵魂上不肯屈服,而且你还活着走了出来,那你不是就赢了吗?那你不就是成就了一个幸存者吗?一个幸存者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就是把你经过的事情,实实在在告诉这个世界。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所以像您说的,您能在这个情况下幸存下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像您这个还不只是幸存。我看您的书,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当时您一个学生,很好的学生问您说,在那样的环境下,怎么保持人的尊严?然后您好像就是说,您在这个环境中,甚至没有写过一次检查,是吧?
要我写悔过书 我写信给华国锋和黄华告状
韩秀:没有。不写,他们逼我在公安局,一定要我写悔过书,说我冲击什么美国联络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中国什么这个那个的,就是反革命行为,而要我写悔过书。把纸摊在面前,笔放在那儿,然后就跟我说,你不写,你就不用想走出去那个门。我说写没问题,写东西我最会了。你知道我写了什么?我写第一封信是写给华国锋,我就痛斥这个公安局的无理,公安局的混账,然后我就跟华国锋主席说,我说我是美国人,我没有别的事情,我只是要回家而已,请你让我回家。
华国锋这是第一封,我还没完,我第二封信是写给黄华,他不是外交部长吗?是不是?所以我就是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在中国已经30年,我历经了所有的苦难,我现在就是要回家。我写完了我就把它交给他们,我说我写完了。他们一看,写给华国锋,他们不能不转,写给黄华他们也不能不转,他们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他们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必须得这样做。他们就转了,我也就走出去那个门了,反正我该写的东西我都写在里头,我痛骂那个公安局。什么东西他们!
过了没有几天,华国锋那边还真有回音来了,说什么此信很好,按政策办。这什么意思啊?不知。黄华那边就阴险。黄华说,这封信我们看了,说的如果某某人要到美国去,他首先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办一个手续放弃中国国籍,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行。这不是圈套吗?我如果说我要放弃中国国籍,没证明我是中国人、中国公民,这种陷阱我当然不会掉进去。我不干,我不理他。就这样。所以不要说是任何其它的地方,什么什么鬼事要写检查,你就是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头,我也不写,我是这么回答的。
主持人:我觉得在当时,如果当时因为要回美国,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就是您18岁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因为刚才不是说到,就是您高中毕业,这个党委书记要您跟您父亲划清界限,说如果划清界限了,您就可以上大学。不划清界限,您就要去山西插队。那个时候您连您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您为什么这么决绝的?我肯定不会划清界限的?
韩秀:父亲的血留在我的血脉里,我没有办法划清界限吧。还有我从小的时候,我外婆是跟我父亲见过面的,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喜马拉雅生命线的工作。我外婆一直跟我说,这个喜马拉雅生命线也好,是当时的陪都重庆也好,他那个时候,她说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最最艰难的时候。
她说而且在美国的支援之下,我们赢了这次战争,对不对?她说你的父亲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和支持者。我从小我外婆就跟我讲这个,她说你在外头碰见的那些鬼事,你不要完完全全地放在心上,你要记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我从小我外祖母是跟着国民政府,她是国民政府工作人员,她跟着国民政府坐船、走路,一直到陪都重庆。那个时候我外婆就跟我讲,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日本人打出去,没有别的。她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在做,而这些美国人在帮我们,其中有你的父亲,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不能为了名利 背叛做人的大原则
我怎么能够背叛我的父亲?我怎么能跟着他们胡说,说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如果我这样去写了,那将万劫不复,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人不可以,不可以做背叛正义的事情,你不能够去背叛一个真正正确的东西。
我只有17岁。不错,一点儿前途都没有,根本看不见光明,但是我不能够做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我父亲,对不起我外婆的事情,我不干。
主持人:我印象中好像您外婆还跟您说,就是背叛这个的人,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吗?
韩秀:我外婆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女人,她说不管是谁,不管哪个政党都痛恨叛徒,连共产党都痛恨叛徒,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违背自己而去委屈自己,委曲求全吧,咱们这么说,委曲求全的话,那真的是没有未来了。外婆说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可以争取去做,而且我们不能够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其实这就是一个传统道德而已,对不对?就是一个传统道德嘛,是不是?
你不能够说是为了利益、为了什么,是为了名利,或者是为了什么其它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去背叛你做人的大原则,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不干。我甚至到了最后了,就是黄华说了,你这做这个那个,而且甚至美联储给了我一封信,居然我还收到了这封信,滕祖龙先生,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
不管中国政府给你什么旅行文件,你都接受,你只要离开就可以了。这是告诉我,不管什么东西他们塞给我,我都可以接受。那个时候他们拚命要塞给我一本中国护照,我不要这本中国护照,但是我没有这本中国护照,我就不能够跨过那个罗湖桥。所以他们一定要塞给我。
滕祖龙先生说:不管什么旅行文件你都拿着,你过了罗湖桥你再把它扔掉都不要紧了,就是你一定要活着走过去,走出去,走进香港,就这么回事。
主持人:您觉得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党委书记要给您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要嘛就划清界限,你就可以上大学,不划清界限你就要去山西。他为什么不直接就是说,因为你成分不好,就直接把你弄到山西呢?发配到山西?为什么要给您这个选择?
韩秀: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如果当时1964年这件事情成功了的话,我还是今天这个人吗?我不也就变成他们的工具了吗?他们还是给我机会,让我变成他们的螺丝钉,对不对?可是我不要做那支螺丝钉,我要做一只鸟飞出去,我要自由。
但是你写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把你的自由断送掉了,对不对?如果我写了那个东西,我今天哪儿还会是今天的我呀?这是不可能的了。今天我什么话都敢说,我什么话都可以说,因为我从来不说谎,我从来不做对不起人的事情。
主持人:所以就像您说的,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想先要把……让您把灵魂出卖,然后他们就……
韩秀:没错、没错、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不肯呢?他说你去吧,死路一条,那条死路等着你。
主持人:就古拉格一样的。
韩秀:古拉格,是一样的,完全一样。新疆就是中国的古拉格,一点儿都不错,你说得完全对。
主持人:在以后我们可以再多聊些新疆和其它国内的故事。但是因为刚才说到您外婆,我很想聊一聊您外婆这个人。我知道您说就是您小时候,因为外婆教您《三字经》、《千字文》,就是很传统的中国的教育。然后也因为外婆的缘故,您跟中国的很多知名的作家有这样的缘分,包括老舍先生、包括梅兰芳什么的。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外婆出生江南书香门第 中国传统大家庭
韩秀:我外祖母是在我的《多余的人》那本书里头有一篇是关于我外婆的故事。我外婆是出生在江南的书香门第里,大家庭。她父亲有六房太太,每一位太太都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地、自己的生活呀。她是第六房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个哥哥下面就是她。很多人现代的很多年轻人,大概看巴金的小说以为这些大家庭都是罪恶之家,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其实大家都太太平平挺好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外婆的母亲家传会修理缮本书,所以这一套绝活我外婆的母亲也传了给她。所以她18岁的时候嫁到无锡,就是她先生家的时候,她母亲也给她所有的工具都带着过去。而他们的婚姻是传统婚姻,两个年轻人从来没见过面,都是父母指定的。
主持人:媒妁之言。
韩秀:我外婆告诉我说他们拜天地的时候,她从盖头底下悄悄地看,看她那个先生有手有脚,她就很高兴他不是残废人。哎呀,好开心的。然后等到他们进了洞房,她先生把她那个盖头掀起来的时候,她都乐得快晕倒。她说那么漂亮、周正、健康的一个男人,哎呀她乐死了。
所以夫妻感情很好,而且她的公公又是一个极开明的大地主。他觉得只有土地不够,这要发展工商业,这中国的前途需要民族工业,要金融什么都要发展。所以就送儿子到日本去,儿子说我受不了日本下女,我太太得跟我去。老先生说,没问题、没问题,你们俩个双双都去。所以他们在家乡先学了日文,然后就到日本去。
先生在前面课室里,布帘子后面都是这些日本太太跟我外婆准备茶水什么。然后简单地说,回到中国之后,在交通银行负责任做事的是我外婆,在家写字、画画、唱京戏的是我外公。
所以梅兰芳指点过他。梅老板,我们叫梅老板,他跟梅老板唱戏,打渔杀家什么的。就梅老板点过他的戏,梅老板也点过他的戏,所以他们唱堂会什么挺高兴。梅先生在抗日的战争期间,蓄须明志,不唱戏,就是不给日本人唱戏,一句话。非常有骨气的。
那时候我外公已经去世了,我外婆已经在国民政府做事,但是因为这么深的交情,因为佩服梅先生的为人,所以也帮过梅先生的忙。因为他养一大堆人,他不唱戏这一大堆人可没法玩了。所以很多人很多人资助他,我外婆是其中一个。那么这样的话49年之后,我就常常有戏票来,这戏票是梅先生给的,梅老板给的。所以我看过梅老板的戏,也见过梅老板的人。
至于老舍先生是在上海接船,1948年9月19日那一天,我正好两周岁,搭乘美国政府送给中华民国政府最后一艘军舰。抵达上海的时候,跟他们,Doctor Sweft & Mrs. Sweft跟他们的小儿子John还有我,我们这四个老百姓都在军舰上。下船的时候接船的人,就是我外祖母和她的表侄女赵清阁女士。赵清阁女士是舒先生的老朋友,也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合作者。舒先生开始写戏还是赵清阁的主意呢。所以说是很好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从小就在舒先生家跑来跑去,就是老舍先生,所以我写小说很多人说你有京味、有舒先生的味。
主持人:所以您在离开北京之前,就是一直时不时地会去老舍先生那里,是吧?但是当时……
韩秀: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64年,1966年他就跳湖了,文革期间。1966年8月。
主持人:当时他有预感吗?就是这个运动的风暴。
韩秀:那个时候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舒先生最后送给我的四个字就是“吃饱穿暖”。他觉得我如果能够吃饱穿暖,我应该就不错了,结果就是我也吃不饱、我也穿不暖,熬了12年。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学写正体字
主持人:所以您跟外婆身边的人还有这一直长大的,就看您写的文字、还有讲的事情、还有您的想法,就感觉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了解的很多。可能比很多中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多。那您怎么看……
韩秀: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传统文化当然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任何文化都有,对不对?但是我的运气好在就是我念的都是特别好的,然后我又起步早,我四岁开蒙。四岁开蒙就《三字经》、《千家诗》、《千字文》就念,然后我外婆她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女人。
她绝对不去一个单位工作,她帮中国书店修书。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残篇,刚刚内战结束一蹋糊涂,都是用麻袋送到家里来。那我外婆就把它捚出来,古书又没有断句没有标点符号的,你得懂得断句,然后你能把它重新修复。修复了以后,再送到中国书店去。
所以在修复的过程当中的那些断简残篇都是我的课本,都是我的课本这个可好了。这我就哼哼哈哈地念,然后照着写,然后学写字。所以1956年中国政府颁布简化字的时候,我早已经能写能读,所有的好东西都吃进去了。然后我外婆就跟我讲,她说这个简化字,这是欺师灭祖。她说绝对不是好东西,绝对是错误。她说你怎么办呢?你在学校里写简体字,一定得写,你不能不写简体字,不行。
你教育还得继续,是不是?然后你在家里头你就继续写正体字。所以十岁的小孩已经人格分裂,而且脑筋清楚。在家里头绝不写简体字,在学校里绝不写正体字,清楚极了。你说说看,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人能这样做,对不对?
韩秀:传统文化……但是共产党的一大堆涌到面前的时候,他还不是得随波逐流吗?他这一随波逐流就不对劲。我的情况不一样,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我看成自己人过。我一直是个外人,我一直是个边缘人,但是这给了我极好的机会。
我站在边上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很多人不能啊,很多人都陷在当中。要升学、要工作、要结婚、要成家、要生小孩,普普通通的事情你都得跟着他们走。你不跟着他们走,你啥都没有,你连房子都没得住,不是吗?对不对。我没这些麻烦,反正老早八早就被他们赶下乡去了,那就拉倒了。等到我从新疆回来,我已经根本没心没肺,绝对不要继续在中国,所以我就往外往回走了,往美国走了。
主持人:所以您刚才说的是正体字,您没有说繁体字。
韩秀:正体字,什么叫繁体字?繁体字是什么东西?繁体字1956年才生出来,正体字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正体字这三个字,这个词汇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可是繁体字是1956年才生出来。
主持人:相对于简体字,中共就说……
韩秀:简体字是简繁,它是对照。简当然比繁好,是不是?它已经有了那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在里头了。它有了简体字以后这非常可怕呀。你想想看有简体字是1956年,195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70年了吧,对不对?快六七十年了。六七十年那是两代人啊,那这新的人们、年轻的人们,如果他不认识正体字,没有看见过正体字。到了美国,你看看他困难不困难,他想看《世界日报》他都有问题啊,是不是?都得找本字典。
因为由简体入繁、由简入正体字是很困难。可是识正体字,简体字很容易,你只要切掉头或者挖掉心或者剁掉手、剁掉脚就是简体字了。可是你只认得那个缺手缺脚的字,回到正体字可不太容易,对不对?你比方说现在有些作者是从大陆来的,他们靠电脑把简体字变成正体字,结果呢?茶几的几就变成几何的几。因为他不知道哪个是对啊!这非常可怕的。
而且你说那些典籍,你比方说《论语》、比方说《资治通鉴》,然后现在出版的都是简体字本。你知道他们删掉了多少?你念的是完整的《论语》吗?绝对不是,因为它一定要删节嘛。你《二十四史》原来这么大一堆,现在《二十四史》变成这么小一块。那些到哪去了?没了。为什么没了?因为它跟共产主义不合拍。你想想看这个传统文化遭受到的不是浩劫是什么呢?
共产党摧毁人的尊严
主持人:所以您好像在一个采访中说,共产党摧毁了这个传统文化。那您觉得它摧毁的是什么东西?
韩秀:这个摧毁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好东西,尤其是一个人,你比方说人的尊严,人应该怎么样做人,在天地之间你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些东西现在到哪里去找呀,对不对?大家赚钱就好了,大家只要没病就好了,还有什么,是不是?房子越住越大就好了。这都不对的了,不是这么回事。
人存于世,它有意义在,对不对?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你看看你现在你去跟年轻人谈谈看,这些做人的基本的道理。你传统价值……你就像文革似的,造反,孩子造父母的反。可是传统文化可是告诉你,你要尊重父母的,是不是?父母爱孩子,孩子要尊重父母,这不是传统的东西吗?
但是文革的时候,他们要说你父母是反革命,你不跟他们划清界线吗?你当然得划清界线,你还得站在台子上去就骂他们。这些东西你以后留下来的这些后遗症,你怎么样去解决啊?
当年曾经批斗过父母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心里头如果还有愧疚的话,那还好。如果没有愧疚的话,他还是个人吗?对不对?你这些事情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不只是说文化、不只是说你看的这些书面的东西、字面上东西,还有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方式、你做人的态度,你对国家、对民族、对人,这一些都是重要的。
人有信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再有一个便是信仰。我爱说这个信仰,很多人都说,喔不能谈宗教不能谈信仰。为什么不能谈信仰?人有信仰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人没有信仰上边没有天、下边没有地,你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不管信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说到新疆的事情。你说新疆的事情这到底为什么?为了什么这一些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弄得惨得不得了?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信仰。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伊斯兰,是《可兰经》,不是共产主义。这共产党受得了吗?受不了,对不对。
你说基督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一贯道也好,这些人他们都有信仰,还有包括法轮功也好,都是信仰。他们有信仰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不相信那个共产主义,这就是关键。我曾经在一个完全没有信仰,把信仰铲除得干净得不得了的社会里,生活了30年。
可是我回到美国以后,很自然地就走进教堂去。我的婆婆去一个天主教堂,她星期天去一个天主教堂,她的孩子们都不怎么跟她去。她穿得整整齐齐,戴上帽子,拿着她的包,准备走出去到教堂去了,星期天。那她的先生、她的孩子们都拿着报纸挡着脸,就我一个人看着她,我说妈妈我跟你去。所以我陪婆婆去。
我们83年到86年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我照样跟我在北京的老朋友联络。其中一位老朋友的太太就是地下教会的负责人。她跟我说……我回美国,我说你要我带什么?我说你这物资缺乏,你要我带什么?她泪流满面,她说念珠。她要念珠,我说没问题。我什么都答应,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已经帮他们买了很多《圣经》回来。
然后我回到Connecticut(康州)看到我婆婆,然后我就讲到这个事情。我说我的一个朋友她需要念珠。我的婆婆端来一个盒子里头全是念珠,她说你把这个送给她,是我的心意。我说妈妈你把这些念珠都给了她,你用什么啊?她说我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生活,我随时可以有新的念珠,你把这些给你的朋友。所以我就全部带回北京送给他们。信仰,太重要了,一句话说不清楚。
主持人:对,所以共产党才拚命地要打压信仰,但是这个东西能给人力量。
韩秀:是底线啊,对不对?你说那些穆斯林,你说那些天主教徒,那是他的命根子他怎么会放弃?不放弃,好,关起来。关起来怎么样?关起来他还是照样信他的《可兰经》,关起来他还是照样地在心里头默念他的圣经、做他的祷告。那是没有办法的。共产主义那种东西是没有办法代替传统信仰的,绝对没有办法。
主持人:所以就像您说的它是人的天性,人跟神的这种关系、对神的这种信仰,它是天生的。
韩秀:人跟神的关系是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人跟物质世界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以及人跟神的关系,就这三大关系组成人类文明,不是吗?这才是真的。
主持人:那非常感谢,韩秀,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特别特别地受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经历也是很值得谈的。包括您回到美国以后,在国务院教中文,包括您在《国家地理》杂志教他们怎么分辨新疆照片的真伪等等。那这些我们就留待下一次访谈,再一次请您来讲那些故事。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
韩秀:谢谢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那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方菲访谈》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