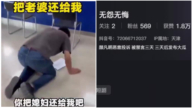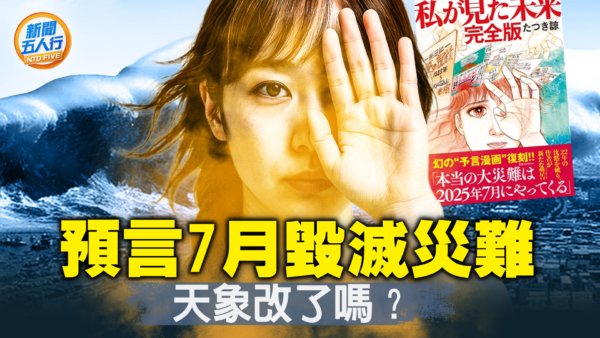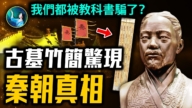一、重新认识“和解、和平、非暴力、不合作”
在“和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么一个系列化的大目标之中,涵盖了和平、非暴力、不合作三个或相关或不相关的分级内容,最近坊间又有了一个新的政治述求,叫“和解”。这一切皆表明了现时民主人以“和”为贵的主流认知,同时也在向世人尤其是主政者昭示:民主人要以“和”来争取中国社会的改变。
现在的难题就是在这个大题目之下,其含义似全部被“和解、和平、非暴力”所占据,而“不合作”一项,在当前的社会情形之下,本来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本应当成为当前所有有志于改变现状者的行为“主旋律”,最后却被遗忘了。
理论上的研究最终是为是行为上的落实。面对中国的特殊环境显得无所适从的“和平非暴力”运动,在没有强大的“硬实力”支持的前提下被动挨打已无立足之地,除了在理论上务虚之外,在现实民主的争取和突破上显然作用有限。
凡事皆不可绝对化,“不合作”运动同样如此。二十年前的那次“和平非暴力”的血肉“实验”,不正是理想主义者们所应牢记的经验和教训吗?
仔细分析,“和解”,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统治者无动于衷,呼喊者积弱难为的现实中,越来越不合时宜;“和平”,在“和解”无望之时,只能做为一个口号和长远的追求,难以得到底层那些最广大被压迫民众的共鸣(特别是被卷入群体事件的人);“非暴力”,面对强权暴政,不能绝对化地杜决,也不能无度地泛滥;而“不合作”,想想也只有“不与暴政统治者进行一切可能的合作”,才能满足削弱暴政所需的绝大多数的条件和要求。
在“和解”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无法给现统治基础以良性改变,也无法给其以致命打击之时,“和平、非暴力”必然无从谈起。从精神到物质的“不合作”运动,是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是不用团队和组织也能实现的行为,是相对而言代价最小的选择,对个人的安全和生存并无大碍,是实现削弱暴政,推进民主目标的较好途径。
国人身在其中,为了生存总难免有“合作”之实,但在生存中找到一个与“不合作”相对应的平衡点,即是良策。
可供选择的方式有很多,如思想上的个性独立,行为上的渭泾分明,工作上的消及切割,消费上的南辕北辙,还有罢耕、罢种、罢工、罢学、罢买、罢卖、罢股、罢市、罢存等等,总之要走一条“一切为了削弱统治基础”的路子,在原先不得已而为之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与之“息交绝游”,少为其输血,多个人积累,从点点滴滴做起,积每个人的小胜为整个国家的大胜,若在其它变革因素成熟时再辅以联合,则必然会形成“东风压倒西风”的大气候,则事可成矣。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几天由中央政府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本来是央府计划要一如既往地将本次经济拉动的成本转至社会和民间,在其无奈加自信的期盼之中,却出现了“沪市”零开张和“深市”微开张的少有局面,说明了国人对目前的国家状况和政府信用的信任度已达历史低点,不再愿意与政府合作“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在危机大潮面前不再愿为未知的政治前景冒此风险,而是采取远离与不合作的态度。--这不就是“不合作运动”的开始吗?
二、跳出“和解、和平、非暴力”的怪圈
暴政长期以来之所以能够如此稳固地坐拥天下独享社会资源,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广大的普通国人在为之做底层的基石,源源不断地为之贡献着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而奉献者到头来反而又沦为被自己供养的统治者所压迫的对象,形成供养–压迫–再供养—重压迫的恶性循环。
“做好自己份内的事”,这是暴政对国民的训化和其得以生存的基石,在不能保证每个国民的公民尊严和权利之时,也是它为国民设下的最大误区。对于专制者来说,当然希望每个人都不谈国事无欲无求,都默默无闻心甘情愿地做它的供血机和螺丝钉,但对欲改变现状者而言,这个“份内的事”,就不再是为它死心塌地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血汗,而是反其道行之,用“不合作”来远离暴政,削弱暴政,最终实现自我。
不论手段是和平还是暴力,目的皆在于要改造现存制度,如果达不到改变的目的,一切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切不可“为手段而手段”,陷入理论的怪圈。必须强调的是,和解与和平同时也是目的,但二者从来都是强者的专利,以现阶段民主人之稚弱,是无资本向强权提出这种“无理”要求的。
打破怪圈的根本手段,就是将每一个人从供养者的队伍中抽身出来。虽然会暂时损失一些现实利益,但这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实现任何一个理想都是有代价的,这符合等价交换的公平原则,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有了付出的决心和勇气,才能有最早最快的回报。
考验一个人是否要真正的民主,还是只为“过过嘴瘾”而罢了的唯一衡器,就是看能否愿意为民主付出代价。当永远的奴才,还是做新生的自我,二者只能选其一。
“纯净是失败者的专利”(杨宽兴)。有人经常高喊“和平非暴力”,却忘记了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民主”这个终极目标。为“非暴力”而无条件地接受强者赐于的“和平”,无形中与暴政进行着密切的配合和良性的互动,在不知觉中将“和平非暴力”运动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不合作运动”彻底地葬送,沦为暴政统治下一个“和平非暴力”的空口号和暴政新的统治基石。这时的“和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追求者,因为在怪圈中不能有所突破,事实上已与放弃追求无异了,而这样的结果,却正中暴政的下怀。
此理论做为一种高端务虚层面的政治攻略和人文宣示尚可,以争取更多的外围同情和支持,但要注意适可而止,不应成为实际行为的准绳和思想束缚。人至清则无用,水至清则无鱼,一心要坦荡而纯洁地追求民主者,不但难以得到世上“最不坏的”民主,就算暂时得到了也无法持久地拥有民主,还不如回转身做象牙塔中的理论贵族,或许更为合适。
三、与时俱进的“分阶段和解”
从国人对现实的种种冷漠和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包括那些走向腐败的人的行为上,皆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普遍潜在的一种对有现制度欲抗无力的矛盾心理。在扭曲的制度下,多数人不是不想高尚,而是无从高尚,在高尚求而无得之时,庸俗与堕落便会乘虚而入,占据信仰真空和道德阵地。再从那么多的人一旦进入如佛门、法门、基督门等信仰领域,便立刻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神奇”效果看,只要有了一个高尚的追求,人心还是向善的,人们还是愿意把握公平,追求正义的。
做为社会形态的一个标志—民主宪政,在纷繁的人类追求中,是得以实现所有个人追求的一个制度保证,所以也应当成为在追求其它信仰之前,所必须要先行追求的一个基础性目标。
“1923年,饱受挫折的孙中山开始对数十年的革命进行反思,法治思想较之以前产生变化并日臻成熟。在该年的1月26日,他与王用宾的谈话里说到:‘然法律是一种理论,至于欲求实现此理论,仍非诉诸实力不为功。’他不再客座总统,而是成立自己的政权,再也不依赖强人,而是成立黄埔军校,训练自己的武装。”—-孙中山借钱革命被称作“孙大炮”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民主也包括和解。为实现此追求之故,虽不一定非要如孙中山那样拥有自己的武装,但为形成广泛的民主联盟阵线,争取各方硬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进行实质性的联合,却是十分必要的。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和解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着的,但为了具备与时俱进的可行性,应该分阶段视事实之需而设定一些必要的和解标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理念,不但要认清各项互为因果的关系,理性地分而待之,还要把握各项轻重缓急的时机,以应对不同需要,切不可从头到尾抱定一个理念而一成不变,笼统地“一刀切”。
现在的“和解”理念,在当前阶段只能是一种策略和手段,与强力争取相配套,将这个道义皮球踢给强者,逼迫他们在政治上有所让步,在将来正反势能相当,民主或将到来时,才能与对方谈真正的和解。
“不合作”运动,展示了“无权力者的力量”,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扩展!虽然理论上不推崇“暴力”,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起码要尊重被极权压迫下的每一个人的反抗权利,这也是争取民主的必须手段。
当一切暴政淫威所仰赖的社会基础—-底层国民不再给其提供足够的养料和血液,以支撑其日渐庞大的暴力机器的时候,这个暴力机器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的暴虐和狂妄就会如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其衰落的命运将不可避免,民主才会真正到来。
2009.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