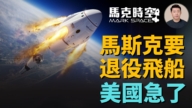【新唐人2011年6月5日讯】 二十二年前我居住在香港,看到国内发生了学潮就返回了北京。有时住在南小街53号,有时住在朋友周舵家里,也在纪念碑上睡到天亮。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我只是旁观者,没有介入。王丹的演讲挤过去拍了照,吾尔开希举旗冲警围也收在了胶卷,司机把一车矿泉水送进广场我也组织群众往学生那儿运,知识分子游行队伍,鲁迅文学院的精英走过来我也拍了照片,佘华他们大都对着我举着胜利手势。但是我没有加入任何队伍。我还去过方励之的家,问他对学潮发展的看法。我仅是这场运动的记忆者。二十二年过去了,能记住的片断已经不多。可以说,那一个月的记忆只剩了十几个小时,而且是依附在胶片之中。
别人呢,那个月都做什么,留在记忆里是些什么?我很好奇。在写《肉之土》的十多年,为了情节,更是逢人便问,试图还原那个岁月。曾在广播学院的林先生在饭桌会偶然说:我这胃病离不了药,就是在广场上绝食落下的。已经成了律师的尤女士在电话中聊到了“六四”,她说子弹就从身边嗖嗖地飞,她爬进了市民的院里,那一个星期自已说不出话,张嘴也没声。为了《肉之土》,我不但要知道那个月每天的气温,油墨的价钱,还要了解有没有可口可乐、口红、指甲油、盒饭以及当年学生们的知识面等等。书和资料堆得有半个屋子才算把那个月显现。当然文学不会重复历史,历史是埋在地下的树根,但写小说必须从根部中汲取养份才能有枝有叶。
历史由多视角组成,一个人的记忆只能是树上的一个叶子,一部书只能是它的一页而已。我们不指望小说会把天安门事件表现出来,这也不是作家的目的。文学只是激活历史,让埋入地下的根长出枝叶,被人们发现。
那么遗忘的结果就呈现了:过去模糊不清,没有必要和现实契合。承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一旦被深埋,再挖出来就是些文物碎片。天安门事件被遗忘就是证据,也是统治者的胜利。失败的大众一方先是气馁,渐渐也就习惯了。今天,除了少数没被击垮的人和受难者家属,多数中国人把六四事件排除在记忆之外,政府恨不得把公历“四日”处理掉直接从六月三日跳入六月五日,但这一天如春天般顽固,总要来临。政府不敢放松警惕。每年的六四都是全军戒备,警察全部上岗不准请假。中宣部全天候工作,不准任何可能激活六四的词汇出现。六月四日的来临中国政府如进入战争状态,他们守株待兔,准备哪儿出事往哪儿赶。这一天全世界的媒体也都瞪着眼,从早晨等到夜晚。双方熬过了这个“特殊日子”才发现:已没有“反面人物”登场了。被颠复的场景只是假想。但共产党也完全明白,坦克碾平人的肉体容易,人的灵魂谁都消灭不了。记忆虽然如掉进深海的飞机黑匣子,真相总会因灵魂不灭而重现。记忆也并不会因为丢失些树叶而树就不见了,它还可以复制传递,还会输送进脑子里原本没这经历的年青一代。因而镇压者无论多么富有就是没有安全感,洗脑者必须死死地记住那些事件,他必须充当样板,以便检验人民之中谁和他一样才能去消灭。镇压者不能给自己洗脑。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个局面,镇压一方为了令人民遗忘反而不能公开提醒人民,那等于贼喊捉贼。最终,当权者成了带着记忆不敢面对历史的罪犯。
我们还看到遗忘的真实: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人熬过了自我审查阶段,便主动认为不应该记住那件事,更不会告诉八九年之后出生的后代了。贵州电视台的朋友说她坚持了两年,不写思想检讨,当然也没有了工作。还有的离开了报社成了二渠道书商。最后,人们便开始投进了挣钱买身份买尊严的经济腾飞之中。十多年过去,也大都被称为“胡总”“刘主席”什么的了。富起来的人成为政府的拥护者,穷下去的成为政府的反对者,但随着财富积累,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就代表制度的成功。再有人要政府平反六四,那就等于是叫公鸡下蛋了。我们当然听到了穷人的不满,他们就寻根碰到了道德被埋葬的天安门屠杀这个坟堆。他们也许知道必须从天安门事件中汲取教训,从历史反思现代,必须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才有希望。也许,但我不信。
我更相信在极权下生存几百代中国人习惯有个政府监督,让他们监督着政府的意识还没有生长。遗忘是顺民的生存法则,他们也是这样教育孩子。我至今没碰上一位家长告诉孩子有天安门事件这段历史。一位北京友人的孩子来英国读书,就因为我告诉了六四真相而成了仇人。“孩子学的是传媒,你让她知道了天安门事件,将来回国万一她嘴不严,那就是害了她。有你这么当叔叔的吗!”他在电话里生气。现在不再来往了。
那么,活的证人都还在,六四事件在网路上就查不到了,图书馆也查不到了,人民和政府双方都互相信守默契,历史就如奥维尔在《一九八四年》中预料的,真的可以消失了。如果有人冒出来说实话,他就是疯子,该进精神病院。敢写出“八九六四”的人就成了造谣者和颠复国家政权的罪犯,投进监狱的诗人师涛、作家谭作人等等都属此罪。真实还包括年青一代对“极少数”的反感,他们认为那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反华阴谋。是的,当国家和个人荣辱捆在一块,说你爹曾经杀过同胞,说你被洗过脑,说你无知,那不等于把自已的名誉给毁了,还怎么去恋爱赚钱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接这话茬。让它消失。
悲哀的是人民比政府还冷漠。历史被遗忘了,没有人去追究已经死去的人了,大家住上了大房子,唱着红歌,早晨去公园跳健身舞活得很好。人民有遗忘的权力,而且也没必要替受害者家属说什么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上访没折迁问题也不用上网控拆。“过好日子又不需要言论自由。再说了,朋友们聚一块,骂起共产党比你们解气,谁被抓了?当今社会够自由的了。”海归们回答我。历史一旦成为过去,人们就会表示不要被“过去”所影响,“你的恨别用在现在,国家这么好了你还恨什么……。”我只好把这类邮件删除,不再和这老同学来往了。我想,每个人都有真实性格,总要回到自己,都正常,不能要求他们永远活在那段时期。
为了解植物人的生理和生态环境,那个夏天总是进出着广东中山医科大学,冬天踩着雪也去北京胡同里住着植物人的家里采访。如今城市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没有人关心穷困的人,那是政府该做的事。好在我的《肉之土》装满了真相,定了格,谁也无法擦掉了。
穷专制容易被推翻,像埃及,那富专制也会崩溃吗?新加坡人不是活得挺好吗?人们希望贫富差距和贪污能让政府垮掉,但极权只所以借来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就是为了巩固权力,让大众失去记忆也是为了政权,政治不改革社会倒退不了,恶政府可以存在下去。民主社会是人民监督政府,专治社会是政府监督人民,虽然相反,但中国人习惯了,能在没有过去的现实里高兴地活一辈子。天安门事件的野蛮暴力使共产党和民间同时失去了对信仰和道德的尊敬,但在经济致富的道路上人民与政府又再次挤在了一起。
遗忘和漠视浸透着鲜血的历史是有罪的,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了祖国。记住历史和记住你的身份是一致的,历史是民族的根。当权者虽然能砍光枝叶,但根总是存在,它是一个民族的根源,而且总会生长壮大,尽管砍杀者把别人关进监狱,但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凶手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不断地重演是因为我们未从中吸取教训,更没有反思。当权者感到从暴力镇压中获得权力是有效的,便一再使用。去年是刘晓波、谭作人,今年是艾未未、冉云飞、野渡等,明年又是谁将被囚禁?
人们有遗忘的权力,但没有抹杀和篡改历史的权力,历史终将把说谎者绳之以法。
转自2011.6.4日《自由写作》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