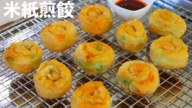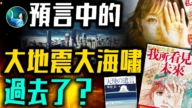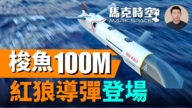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3月8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孙中山坚持革命 反对改良 志在建立民国 “于斯竟成”
一 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具体表现在:
(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注十八】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注十九】同时,他还从欧洲一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注二十】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注二十一】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注二十二】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注二十三】
(四)“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注二十四】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注二十五】
二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然而,“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为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着清王朝的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注二十六】二是开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新政,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注二十七】一时间宣传欧洲革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排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注二十八】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质。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注二十九】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义精义,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对此,孙中山自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注三十】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之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和五权宪法之民主建国方略的成熟及传播,使得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从而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结束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定夺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汉人当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废除君主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注三十一】 他还说:“这次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注三十二】
从此,由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同一”。只是就范围而言,中国国民革命才较作为其本体内容的中国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内容的广泛性,即外反列强欺凌和内反满族专制统治之民族革命内容的加入。本书为标明中国民主革命乃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本体和本质,故在全书的章节标题上,决用中国民主革命这一概念,以使中国民主革命获得她在革命性质上的明确性。但又在全书的内文里面,部分地沿用中国国民革命的概念,以求在行文之中,表现她历史过程和历史内容的真实性。
三 革命与改良的两场大论战
第一场大论战发生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
如果说,自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始的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为追求富国强兵而推动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历经清政府数十年的经济改革,和康、梁等对于政治改良的追求、实践及失败,而终于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共和主义思潮的兴起及民主革命目标的确立,奠定了必要历史基础的话,那么,戊戌之后,恰恰是在民主革命的理念和目标已经愈来愈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历史追求时,一九零二年,由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所公开挑起的保皇改良派对民主革命派的大论战,却遭遇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对于保皇改良派的第一次大反击。
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歌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尤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杀人放火而已”,所以,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注三十三】其后,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而“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年轻的民主革命家吴樾不仅畅言“反枝叶改革、倡非常改革”,更以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来表明他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的精神,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则著有《革命军》遗书,竭力赞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扫除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的积弊”。又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陈天华则以“壮夫跃海”的英雄行为,用年轻的生命敲响了他的《惊世钟》,希望追随专制改良者们能够《猛回头》。
在这一场对保皇改良派的反击战中,民主革命派除掉揭穿了前政治改良派“彼之爱国,无非是爱专制政体”的本质,尤其批判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君主专制法统,和旨在维护这一法统的封建礼教道统,指出了“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至死亡不止”的残酷专制本质。不仅有力地轰击了宋明以来意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学基础;而且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与改良的那一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大论战,铺垫了共和主义的思想基石;更为辛亥以后中国知识界发动那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其对孔孟思想文化体系中专制思想文化成分的批判和清算,埋下了历史性的伏笔。
第二场大论战始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
一九零五年底,面对着清政府诱改良以灭革命的阴险手段,和政治改良派要君主立宪不要民主立宪的顽固立场,民主革命派早在《民报》创刊伊始,即指名道姓地指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为满清政府制造“欲使吾民族诚心归化之立宪改良论的祸水”。【注三十四】
一九零六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了“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将两文合刊出版,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对革命派展开全面反驳。大论战势在必发。
梁启超主张改良和反对革命的重要论点,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指清政府 —— 作者按)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
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注三十五】然后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又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昔存于理想,今现于实际。心理之感孚,速于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于革命前,革命后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注三十六】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的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望之于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注三十七】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干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注三十八】
就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杀人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注三十九】
此后,各家民主革命派刊物,乃于中国本土和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参加了这一场大论战。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纲领,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的民主革命思想,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和要不要建立一个主张民权的民主共和国”等大是大非问题,对立宪改良派“只要改良、不要革命”,“只想哀求清王朝立宪、不想推倒清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等错误思潮,特别是针对清王朝“虚以敷衍改良、实为扑灭革命,立宪为假、专制为真”的维护专制手段,予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批驳。胡汉民在为《民报》纂文时便写道:“旧日为异族政府所有者,固当倾覆之;而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政府,亦必同时改造而后可以保存而竟存。”同盟会员汪东亦发表文章呼应说:“单纯的杀人放火,根本谈不上是革命,乌可以辱我庄严、宝贵之革命二字。”【注四十】《夏声》与《河南》两家杂志,更从清王朝四十年来推行改革开放和空喊立宪入手,驳斥立宪改良派们说:“四十年来,言新法者,非今日之政府乎?无日不为之,而究其所为者何事?新法之收效于今日者安在?有能举起大者示之于人乎?……夫以如是之政府,而日日言立宪,五年,十年,十五年之预备期限,常视吾民之举动如何以为伸缩。而又于立宪预备之时期,宣布言论集会之苛虐条件,以为摧抑吾民之具。”【注四十一】而且,“以预备立宪时代即演出如许惨祸,吾不知实行立宪,则民祸将伊于胡底也!”【注四十二】“国民之普通自由,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保护之,乃反于预备立宪时代剥夺之。国民政治上的权力,彼不能于预备立宪时代促进之,反于预备立宪时代限制之。非丧心病狂,奚为行动不伦,一至此极!”【注四十三】
由是,革命派乃对改良党人批驳曰:“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以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泣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也。”【注四十四】鼓吹共和的《醒狮杂志》在《醒后的中国》一文中,就曾指责一心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派为“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尤颂圣朝恩”。《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则以“不到临崖绝命时,强权政治有谁知”的沉痛呼喊,期望改良派能够在强权统治的迫害中猛省过来。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名声卓著的《河南》杂志尤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杀人流血之直接了当也!”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大清朝不改”,非但穷于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注四十五】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后,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号召“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共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一些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因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是在要共和还是要专制和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战胜了改良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四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她的高潮期 并且“于斯竟成”
上述的两场大论战,特别是后一场由革命派挑起的,对改良派的大批判,不仅使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改良派锋芒失尽,而且使立宪改良派在对革命派和清政府的两面作战中,痛苦地迎来了它们最终的失败和分裂。由是,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起义。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干,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矣!”【注四十六】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注四十七】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楷模。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注四十八】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务”。【注四十九】安庆新军起义烈士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革命党……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尔细思之!”【注五十】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注五十一】青年革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刘慎终、喻培伦、宋玉琳、陈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难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注 释
【注十八】 参见〔美〕史扶邻着《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
【注十九】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注二十】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注二十一】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注二十二】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注二十三】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注二十四】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注二十五】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
【注二十六】 《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注二十七】 《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注二十八】 《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注二十九】 《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注三十】 《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第八章。
【注三十一】 孙中山:“于民报发刊大会上的讲演”
【注三十二】 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的“军政府宣言”。
【注三十三】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一九零四。
【注三十四】 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号第二六页。
【注三十五】 第一条:《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第二条:《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第三条:《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第五条:《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第七条:《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以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第十一条:《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等。
【注三十六】 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第二八至三十页。
【注三十七】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第五四页;“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四号第二八页。
【注三十八】 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民报》第七号第五十、五四页。
【注三十九】 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九号第四六、四九页。
【注四十】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汪东:“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
【注四十一】 皮生:“策国民之前途”。《夏声》第五期。
【注四十二】 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河南》第五期。
【注四十三】 明民:“预备立宪之矛盾”。《河南》第三期。
【注四十四】 征轩:“专制君主又将去其一”。一九零九年四月二七日《中兴日报》。
【注四十五】 《民报》第五号第一四零至一四一页。
【注四十六】 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注四十七】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
【注四十八】 《辛亥资料丛刊》。
【注四十九】 《辛亥资料丛刊》。
【注五十】 《辛亥资料丛刊》。
【注五十一】 《辛亥资料丛刊》。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