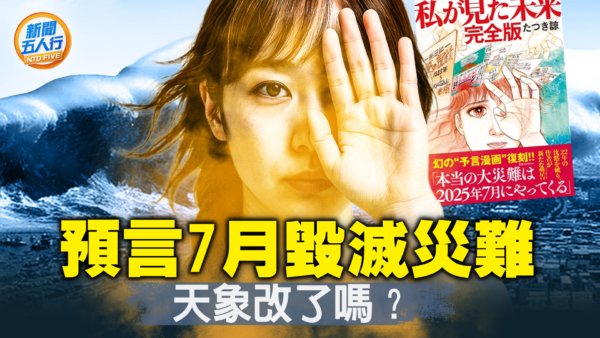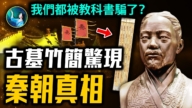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3月21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第三 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注三十一】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注三十二】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注三十三】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Q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以重创,特别予刚刚诞生、还在鲜血和痛苦中挣扎的新中国,在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进了新鲜的历史气息,使之迅速地出现了推陈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崇尚自由、反抗权威,排斥专制、追求民主,批评传统、肯定现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学,深怀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积极、不要消极,要个人主义、不要专制主义”之种种崭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在迅疾地改变着那个时代的面貌,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因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更为久远的历史范围内,将它视作在各个方面均要推陈出新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也就言之不过。
第四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一、文学革命方面。由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成分 —— 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于刚刚认同科学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样背负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辛亥之后的中国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既身置其时,又身在其中;因而,他们对于时代发展的本质,也就很难认识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旧时代为旧文化所培养起来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由专制复辟所造就的社会灾难,和由刚刚覆灭的专制王朝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痛苦,与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联系起来,甚至反转过来认为,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成功所致。这就使得鲁迅等一批作家于文学革命后期,将对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批判与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时代阵痛划了等号,不仅混淆了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的政治界限。从而为不仅要推倒专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作了文学上和心理上的铺垫。比较一下法国波庞王朝复辟时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伟大作家,重新认识一下他们在文学上一心要批判的复辟贵族,竟恰恰是他们在政治上一心要维护的心爱者 —— 这样一个“根本矛盾”,我们就能明白,他们对复辟时代社会心理与时代风情的描写,实在是对那个“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时代,作了相当本质、相当鲜明,即相当深刻和准确的文学概括。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 —— 应该说,正是从这些不朽的文学形象身上,我们才看到了法国社会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激烈冲突,以及这个冲突之必然要解决和必然能够解决的历史前途,即“圣·玛丽街修道院里的共和主义英雄们”一定能够战胜专制复辟的胜利前景。这固然是法国文学已经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样是法国民主革命前漫长的思想启蒙运动,曾对专制主义实行过广泛深入批判的一个积极成果;更是法国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并正在解体,民主与科学已经先走一步这一历史进步性,所带来的进步文学现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于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革命范围内,没有能够积极地区分传统思想文化与其中“专制思想文化成分”的界限,从而将所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都当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就不仅为对手的反击带来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公正态度,更为嗣后在共产革命思潮的侵扰下,不加鉴别地动辄便要否定和打倒传统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传统文化来取代对于当代共产专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愿批判共产专制政治,却乐于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并坚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奇异文化现象,虽然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而已,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文化现象,却在维护共产专制制度,鼓吹共产专制体制内的政治改良,淡化共产专制制度的罪恶,特别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对新一代青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新文化运动“负面影响”的一个至为悲哀的历史效应。
注 释
【注三十一】 一九一五年“胡适致梅觐庄信”。
【注三十二】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注三十三】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北京政府教育部曾通令全国,要求各级学校的教材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