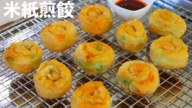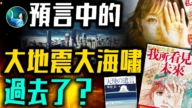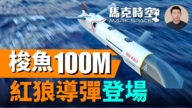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4月24日讯】 【《谁是新中国》题解】 谁是新中国?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后,又会出现长期的内乱和内忧?虽然能够一再地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又惨败在1945—1949的内战之中。嗣后,竟能够在台湾完成向民主的全面过渡,使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的理想得以实现…… 如果是后者,为何又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全面复辟专制制度,虽然迄无外患,更无内忧,却造成“冤狱遍中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局面,为漫长的中国专制制度,补上了中世欧洲“教政合一”式极权专制统治的血腥一课。待到风雨飘摇之时,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开放”,然而,其成就虽不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其命运却与清王朝一样而不能免,其腐败和腐烂,更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
(接上期)
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 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注四】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注五】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注六】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 “九一八”枪响之际中 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二、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抗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族之祸。
注 释
【注四】 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叛变时,国民党将军、中共地下党、时任白崇禧参谋长的刘斐,曾对陈济棠如此说。
【注五】 一九三三年陈济棠拒绝中央调兵赴赣剿共时所说的话。
【注六】 蒋纬国:《蒋委员长十四年抗战指导》,八十二年讲于国家统一建设促进会。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