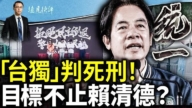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12月12日讯】改革,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此所谓朽木不可雕也。一般地说,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变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它也带来了新旧价值观念的强烈冲突和碰撞。由于新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一时难以建立,新旧机构又处在不断调整、重建之中,改革中的腐败行为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已成为社会的一种风气,上至中枢,下至僚属,无不公然贪污受贿,也就是说,整个统治机器已被腐败侵蚀,法律不足畏,官常不足守,那么不仅仅是改旗易帜的问题,而是国家机器到了该重建的时候了。
一个多世纪前的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改革,是20世纪初清王朝在历史抉择的重要时刻被迫进行的一场与传统的封建社会改良自救运动有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改革,它是当权的统治者力图利用传统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自上而下地进行体制与政策的改革,以期保持原统治的连续性,又和平地实现政治与社会结构革新。其涉及的范围之广和触及的内容之深前所未有。应该说,历经10年的改革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
然而,由于王朝的腐败最终导致改革的彻底失败,清王朝在改革中寿终正寝,也使中国失去了挤入世界强林的机会,那么腐败是如何导致这次近代化改革失败的呢?
一、清廷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延误了新政破旧布新的时机。
到了近代,君主专制与皇族集权是政治反动腐朽的典型表现。清末,封建专制已到烂熟的程度,可是满清政府在20世纪初世界近代化大潮汹涌澎湃中被迫实行新政之时却仍不忘记借改革之名行封建集权之实。
而近代化的理论认为,社会的近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是社会的各个方面携手共同向近代社会前进的过程。文化教育和经济的变革必然产生与传统社会根本不同的异质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期望值的根本改变,也包括新的阶层和政治派别的形成。这就必然会对现存的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和政体的有效性产生强烈的冲击和挑战。统治集团能否扩大参与权,将这些新的因素吸收到政权中来,不仅是其政治凝聚力能否继续得到维持的关键因素,也是政治秩序稳定与否的必要前提。而且近代化是一个多层次的演变过程,近代化一旦启动,它在使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发生变化的同时,也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革新。清末新政以文化教育和经济改革发其端,它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嬗变和新的阶层的形成,必然要求将变革引向更加深入的轨道。1906年预备立宪方针的确立,就是这种推动的结果。
但是,新的阶层并不满足于政治改革的一纸空文。它所要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参政权。统治集团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对政治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造,是其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政局能否稳定的基本因素。统治集团只有放弃一部分权力给这些新的阶层,扩大统治基础,才能维持其统治。可惜的是,清王朝腐败透顶,虽然在外力压迫下被迫实行了新政,但是满清王朝一味坚持君主专制与皇族集权,不愿实行一丝一毫的民主。1907年成立的号称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只不过是点缀门面的装饰与不折不扣的清谈馆而已;1908年8月清廷颁布的5钦定宪法大纲,只不过是把君主专制之权力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中央官制改革打破了满汉平均的各部大臣的任命,表明清廷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向满族集权的方向倾斜,而1911年5月出台的皇族内阁更将清廷的集权政策发展到顶峰。结果引起了立宪党人的背离与倒戈。作为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宪派曾对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抱有很大希望。但是,预备立宪以来,清廷的一系列举措使立宪派对清廷由支持转而失望。而清政府对国会请愿运动的无情镇压,在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冥顽不灵和为保专制而丧心病狂的面目的同时,也宣告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至1911年反对皇族内阁遭到严厉申斥,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违背立宪政治,拒不改正,立宪派越发感到政府无药可救,思想认识发生飞跃,由昔日的抵御外患为主一变而认为铲除内患最急,坚决主张打倒腐败专制的政府。他们公开发表宣告全国书,阐明满清王公亲贵组成的所谓内阁完全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
这样,本应赢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却由于满清统治者的举措乖张,愈来愈引起国内政治力量对清王朝的痛恨。清廷借改革集权皇族排斥汉人的一系列行为,使汉族官员心灰意冷,他们不仅不再像往日那样死心塌地效忠清王朝,而且常利用当时的社会力量向清廷施加压力,竭力鼓吹发扬民气,藉人民之后援以抵抗中央,清廷之失坠,其近因以此为着。随着革命斗争形势日益高涨,本来支持清廷改革的立宪派相率背离朝廷,有的直接转附革命营垒。
总之,清末新政期间清廷极端的专制与皇族集权阻断了新政的实质性进展,也延误了近代化的大好时机。由于清廷拒绝通过参政权扩大的途径将新兴阶层吸收到政权中来,其权威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理论的依据和阶级基础,当清廷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宣布缩短立宪期限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
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
督抚专权,清廷中央权威衰微是太平天国战争的后遗症。而清廷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役中的失宜举措,使其政治权威再次受挫。正如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在1901年7月17日写给莫理循的信中所谈到的:现在还有谁人将总理衙门盖章的护照看得像某个总督签署的护照那样有效呢?你大概还记得两广总督曾经告诉我,总理衙门只能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敢命令他。事实上,除了皇帝外,连军机处也不能对一个总督下命令。在紧急情况下,像我们去年夏天见到的那样,如果皇帝依照错误的奏章发下圣旨,总督也可以不服从。督抚专权,架空了中央。而清末新政的展开,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权作支撑。中央政权的软弱无疑影响了其在改革中的作用的发挥。
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近代化获得成功的前提和保证。但是,加强中央政权并不是集权于皇族,而是必须将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尤其是推动立宪的立宪派和绅商纳入到集权的政治体制中来,建立一个获得各阶层普遍支持的强大、稳固而有效的国家政权,才能团结大多数,保持社会稳定,共同推动社会的近代化。否则,政治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一个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既应保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又必须有适当的地方自主权,而实行君主立宪就可能达到这双重目的。新政期间,
尤其是预备立宪本来给清廷调整几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由于统治者的思路没有随政治改革的时势而调整,慈禧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年轻的满族亲贵们却只是借改革削减地方权力,一味集权中央,借机加强君权与皇权,加剧了地方势力对清廷的离心倾向,使自己愈加孤立。从他们最后两年多的表现看,他们不仅要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而且要收回汉人的权力,使之统归满族亲贵。
到成立皇族内阁时,满人专权在形式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同时,汉族大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却因此对清廷已经大失所望,他们大多数已不准备与清廷同舟共济了。结果,大清王朝人心尽失,危急之时,无人力保,使王朝走向了不归路。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宣布脱离北京的重大原因,就是长久以来由于君主专制与皇族集权而造成的地方势力与北京朝廷的离心离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末地方势力的膨胀非但不是一日形成,而且在许多方面有相当的权力。督抚作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他们支持改革,但清廷力图以此为契机,削弱他们的权力以加强中央对权力的垄断的做法引起他们的反感。督抚坚决反对集权中央,坚持地方拥有权力。咨议局的成立,又使绅商权力得到膨胀,使中央政权更加被削弱了。清廷在谕旨中反复强调决议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这种对中央权力的强调,实质上反映了其权威危机的严重。由于督抚的坚决抵制,许多新政措施无法推行,如议改官制,湖广总督张之洞议复一电,一则曰财力竭蹙,再则曰经费太巨,三则曰安有余力筹款等语。因此,清廷的集权计划终于夭折。而官制改革在双方关系上投下的阴影却成为日后王朝危亡之时督抚不愿效忠的症结。清廷欲借改革之机,收回督抚权力归中央,加剧了督抚与清廷的矛盾,立宪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参与政权的愿望落空,于是督抚与立宪派的态度趋于一致。督抚倒向立宪派,督抚和绅商离心倾向的增长并转而反对清王朝,使清廷遭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在预备立宪运动中屡遭挫折的地方乡绅的离心倾向,则使在传统社会中历来是王权统治基础的这部分成员现在与政权之间的权力平衡受到了破坏,其结果是:被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不能进入政治系统,其激进阶层或加入军队,或与会党结合,走上革命道路;由于政治参与的速度、力度大大增加,覆盖面迅速广泛,造成权力的分散。但这种权力的扩大与分散,既不能维护原有政府的权威,又不足以加强权力运作的效果,参与这一活动的士绅则因资政院、咨议局作用被限制而使进入中央决策的渠道被阻塞而与政府日渐远离。在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扩大的同时,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大加剧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三、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经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天下之财,悉应赔款,清朝财政早已是油干灯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清末新政中清廷又不分轻重缓急,不分主次,什么都改,使本已紧张的财政更加窘迫。财政的窘迫不仅使新政的筹备不能按期进行,而且使清廷以筹款为急务,而筹款除加捐加税外,别无善策,结果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捐税过重,种类繁多,以致无物不捐,不时不捐。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而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不顾百姓死活,任意苛敛,更是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其中尤以抗警捐、学捐的斗争最为广泛,捣毁警局、学堂的风暴遍及各地城乡。据统计,在清末最后十年中,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呈直线上升趋势,1905年90次,1906年160次,1907年190次,到1910年发展到285次。如果说改革的不分主次与轻重缓急加大了清朝的财政压力,捐税增加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反抗,那么,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则使社会风气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更加大了人们的反感情绪。在新政的推行中各种卑劣的心机与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出来。
梁启超指出:清政府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单。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慈禧,作为最高统治者,历来贪得无厌,腐败至极,新政中更是大肆收受贿赂。继慈禧之后主政的载沣虽然政治上无所作为,但收受贿赂却比慈禧有过之而无不及。奕勖作为首席军机大臣,竟以贪赃枉法著称于世。整个官场上行下效,贿赂成风,腐败透顶。有人慨言:自明降谕旨改革官制以来迄于今日,大小臣工,徘徊瞻顾,虚悬草案,施行无期,而昏夜乞怜,蝇营狗苟,其风益炽,清议不足畏,官常不足守。上则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噬善类。正如梁启超说: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人民之脂膏以自肥。自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刮无余,商业萧条,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加上水旱灾荒,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来任何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罔惜民艰,遂引发人民对改革的普遍不满和反政府斗争。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间,以抗捐税为内容的民变遍及全国城乡。
除了反对清政府的苛捐杂税,城乡人民的相当一部分斗争的锋芒是直接针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清廷谕旨说,各地抗捐频繁,推其原故,总由不肖州县,挨户摊派,甚或侵蚀入己。劣绅胥吏需索中饱。谕旨意在推卸清政府自己增赋剥民的罪责,但地方官胥绅棍的刁难苛虐和需索中饱,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此起彼伏的民变给人们展现了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却给反清革命造成了强大的声势,推动了反清革命斗争的高涨。此时,满清王朝在其统治阶级内部早已分崩离析之时,被统治阶级又在外部动摇着她的统治根基,满清政府四面楚歌,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倾覆之势已成定局。国家之坏,在乎官。新末新政中,官场腐败,而政府又苞苴科敛,则正如粪土之坏,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滋长而暗长呼?晚清的官场,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中小官吏,地方豪绅,几乎无不腐败。整个王朝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举国皆贪,官与官之间相互勾结相互利用成为王朝行政机器得以运转的润滑剂,人心所趋向早已失去了传统道德的制约,银子成为整个社会异常活跃的动力,也成为权力系统着迷人魔的追逐目标。当一个政权或一个政权组成的成员们,在他们无所顾忌也无所制约地收获腐败的利益时,就必然失去从根本上维系一个政权赖以生存的人心。在世道的变迁中,人心的离散是决定清王朝命运终结的根本。
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府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的痛恨。因此,当武昌起义爆发后,它很快得到各阶层的响应和支持。总之,清廷的腐败透顶加速了人们对其幻想的破灭,导致了清末新政的失败,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专制是覆亡政府的导火线,极端专制与腐朽的制度决定了这样的政府是不会把改革认真进行下去。
如今,专制腐败透顶的北京当局也在叫喊政治改革,但它在千头万绪、矛盾丛生的形势之下是无法驾驭全局的。如果无法在政治改革中放弃一味集权而保持权威的连续性,尤其是对改革的关键部分如司法独立、人大、政府和执政党的相互制约关系方面做出正确处置,而是一如既往地敷衍、拖延、或出于舆论的欺骗而作作秀而已,那么,到头来其作伪只能挑起了更大的国民之怨,使执政党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其结果不但会使经营十年之久的维稳工程付之东流,并且其专制政权走向崩溃也是必然的结果。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