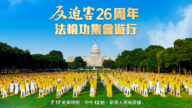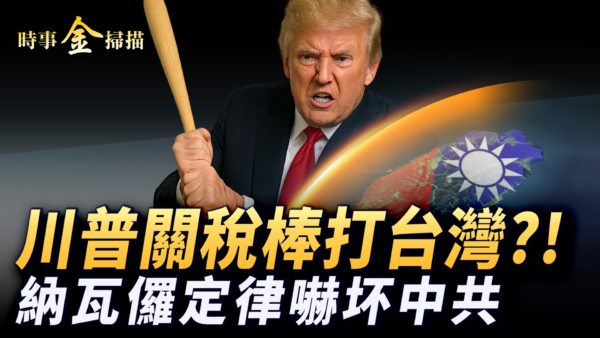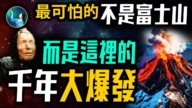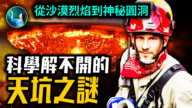【新唐人2013年6月8日讯】24年来,许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六四”惨案是否不可避免?如是,类似悲剧将来是否还有可能重演?
应该说,正是“六四”惨案肇事者邓小平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当年,“六四”枪声尚未停息,北京城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邓小平就匆忙宣布了他对事件成因的哲学化解释。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此处“风波”是对89天安门事件的非正式简称,正式的“提法”非常吓人,全称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邓小平的意思是,既然“动乱”、“暴乱”“迟早要来”,无论如何躲不过去,那么“平息反革命暴乱”也就非做不可,无从避免。换言之,“风波”是必然的,镇压是必须的,惨案是难免的,这一切早已注定。邓似乎不仅仅是在玩弄“历史唯物主义”的陈旧词藻。把一个人为制造的惊天悲剧轻描淡写地归因于“环境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对于思想者,这是偷懒;对于政治家,这是麻木;对于肇事者,这是诡辩。
邓小平接着又说:“(这场风波)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照他的说法,这不过是一场“一定要来的”“风波”如约而至罢了,而且来得不早不晚、恰逢其时——正好赶在“一大批老同志”离世之前,无数年轻活泼、才华横溢的生命就这样栽在了风烛残年的“老同志”手里。邓小平没有为军人射杀学生和市民表达丝毫的愧疚和难过,反而认为此种结果“对我们比较有利”。这不禁让人满腹狐疑:在邓小平眼里,莫非“六四”是一出街头杀敌的大喜剧?莫非这又是1957年曾经上演过的老剧目“引蛇出洞”、“围而歼之”那一套?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那样,“要闹就让他们闹个够,他不闹,你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直让他们闹到赵紫阳们耐不住性子,自己跳了出来,“老同志”们受不了刺激,再也坐不住了,此时正好顺势祭出“专政”法宝,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去狠狠收拾他们,而邓小平所要做的只是“阳谋”而已,冷眼闲看学生们按下“历史必然性”的按钮,欣然坐等“老同志”们送来“比较有利”的收获。
不,事情并不是这样,邓小平的话也不是这个意思。邓没有那样阴险狡诈,也没有那么悠闲自在。在那一段峥嵘岁月里,邓和他的家人其实比所有的中国人都更加惶恐紧张,他对民众的恐惧远远超过了民众对他的恐惧,至少在开枪杀人之前是如此。邓小平说那番话的意图诚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高瞻远瞩、未卜先知的“经验和智慧”,也不是为了表功,而是为了卸责。他是要让“大气候”、“小气候”和“一大批老同志”一起,替他分担屠戮平民的罪责。但邓的话貌似有理,却根本经不起推敲:既然早知“风波”势所必至,何不早定预案,早作准备,有条不紊,从容解决?何以如临大敌,如丧考妣,手忙脚乱,惶惶不可终日?
再者,邓将“一大批老同志”拉出来为自己垫背,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老同志”本非铁板一块,和邓一样热衷于“专政”的强硬角色者固然大有人在——如王震、薄一波、李先念等人;不赞成军队进城、反对开枪镇压的同样大有人在——如徐向前、聂荣臻、张爱萍、萧克等诸多军中将帅,还有“今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这些人的政治份量并不轻。就连一向被人与邓同列为“‘六四’罪魁祸首”的杨尚昆、陈云,据蒋彦永医生透露,也曾私下里对“六四”镇压的方式和手段颇有微词。料想当年陈云对于“平息反革命暴乱”、杨尚昆对于“火线倒赵”的重大决策并非全心全意支持,内心里或多或少是有所保留的,之所以不便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异议,或许是担心受到邓的排挤打击,或许是出于“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之类不得已的苦衷。在共产党里,可以做错事,不可站错队;可以整错人,不可跟错人——这就是所谓的“组织性”和“党性”,所以,每到善恶对峙、正邪对决的关键时刻,认人不认理的情形总是反复发生:明知彭德怀是对的,还是死忠毛泽东;明知刘少奇被冤枉,仍然合伙往死里整他;明知军队不应该杀平民,还是表态支持邓小平。结果,“一人发昏,全党作孽”变成了家常便饭。
除了“老同志都支持平暴”之外,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一派胡言。从“风波”到惨案,从台前到幕后,对于最终的悲剧性后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恰恰正是邓小平本人及其帮凶们的杀人意志,而这也正是85岁高龄的邓小平所不敢面对、并试图竭力掩盖的事实。
回首24年前,“4∙26社论”和戒严令是当时事态升级和恶化的两个转折点。“4∙26社论”之前的学潮主题是悼念胡耀邦,为其鸣冤叫屈,4∙26之后学生自治组织被迫自卫,为摘掉“4∙26社论”所扣下的“动乱”帽子而将街头行动不断升级;戒严令更一举改变了整个事件的和平妥协前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真诚倡导者赵紫阳成了戒严令的第一个牺牲品,民众与政府之间尚有诸多回旋空间的政治互动变成了直来直去的政治对抗。而众所周知,“4∙26社论”和北京戒严均由邓一锤定音,都是邓小平的杰作,是其强权意志在八九事件中的集中体现。至于开枪清场的屠杀命令,毋庸置疑是由邓小平所下,因为别人没有这样的权力,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魄力”。综观八九运动全程,其主要的变化轨迹无不以邓小平的强权意志为转移。
事后看起来,邓小平那篇“六四”解说词全然没有道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当然不止一种走向,也不止一种结局,流血惨剧更绝非早已注定、不可避免。如果不是邓小平而是赵紫阳主导中共决策,结局当然会大不一样。如果没有“4∙26社论”而有政治改革的明确表态;如果没有戒严令而有更多更真诚的朝野政治对话,惨案自然也就不会发生,结局甚至可能会皆大欢喜。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共当局与抗议示威者之间永远也无法达成真正有效的妥协和谅解,但是只要邓小平真心不想杀人,他仍然有一千条办法、一万种手段去和平解决天安门广场上的冲突,因为他的手上并非只有军队这一枚棋子儿,他的资源多得很,筹码多得很,完全没有必要对和平的民众抗议运动反应过度,也完全没有必要在武力解决这一棵树上吊死。
邓小平是个精明人,即便已经85岁,也没有真的老糊涂。陈希同说他没有资格到邓府去“谎报军情”,其实即使那些有资格到邓府请示汇报的人——比如李鹏—— 曾经向邓“谎报军情”,也未必骗得了邓小平。邓的子女、秘书和亲信不仅另有可靠的消息来源,甚至也有撇开官方向学生领袖直接传话的渠道。邓小平当然很清楚,所谓“坏人”、“黑手”、“西方反华势力”并没有能力操控中国的学生运动(中共官方“平暴报告”竟然将方励之等人的某封私人请愿信、香港杂志上的某几篇文章、某美国智库的某份研究报告、美国之音的某几次广播、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的某个讲话通通视作北京学生运动的思想和组织渊源,此种“阴谋论”真是荒谬绝伦,滑天下之大稽),北京的校园和街头并不存在什么“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游行示威、绝食静坐的学生们并没有那么恶毒,要“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邓小平语),长安街上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反革命暴乱”;邓小平当然也很清楚,如果军人不进城开枪,如果天安门广场不强行清场,事情也会慢慢转圜、慢慢解决,学生不会老死于广场,中国不会神州陆沉,从此“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下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邓小平语)。问题仅仅在于,邓小平和他的党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对公开抗议过于敏感,过于恐惧,不能适应,更不能善待,他们对民间反对势力过于苛刻,过于残酷,严防死守,视如仇敌,他们已经养成了仰仗暴力、迷恋专政的恶习,而且真的是“死不悔改”(此为毛对邓“走资派”所加的定语)。这就是“六四”惨案的主因。如果邓和他的党没有染上这些恶习,“六四”悲剧断然不会发生;如果将来的执政者改掉了这些恶习,“六四”那样的悲剧自然完全可以避免。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