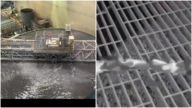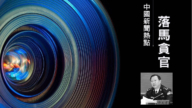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2月22日讯】中共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丑闻,备受舆论关注。12月2日下午,朱军性骚扰案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但法庭拒绝受害人弦子(网名)公开庭审的申请。12月21日,弦子发表长文公开当年朱军性骚扰的全部经过,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以下是《弦子:2014年6月9日发生在化妆室的全部经过》全文:
从2018年主动站出来到递交法院申请,我一直有一个最坚定的诉求:希望可以得到公开审理。
希望公开审理,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经历、我的诚实,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
虽然,从2014年到如今,我已经向公安、向法院讲述过许多次经过,重复这件事,对我来说本身就是折磨;虽然,无论我如何回避,被性骚扰的过程依然给我一种性的耻感——在所有人都看过我的当下。我总担心人们看到我时会想起我在化妆室的狼狈与弱小,性侵受害者的身份,会永远成为我的标签。
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想要公开审理,想要将我的痛苦、我的遭遇摊开给所有人看。因为,个人感受必须为正义让步,我愿意公开审理,愿意公开全部证据、公开我被朱军性骚扰的经过,公开所有那些耻辱的细节。
只是,从2018年至今,我们要求公开审理的诉求从未得到过批准,出于对法院、法律的尊重,我恪守诺言,保持沉默。出乎意料的是,近日却不断有人对当年案发情况进行断章取义和恶意歪曲,变成对事实的诋毁、对我的辱骂。
虽然痛苦,但若要求索正义,就必须坦诚,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六年,记忆难免会有疏漏,但我所回忆、所讲述的,都是发生在我身体上的事实。
哪怕我要对所有人,做一次公开的“笔录”。
1.
2014年6月9日,正在艺术人生栏目实习的我,需要完成导创老师布置的作业:将实习经历拍成记录片,老师还强调,我们最好能够采访到重要人物,就比如朱军。
那天,先于我来到台里的实习生商同学说要去化妆室找朱军,因为知道他和朱军接触较多,我告诉他我想要采访朱军完成作业,商同学让我和他一起去化妆室,帮我找机会采访朱军。
当时,朱军独自坐在化妆室,身边有一把空椅子,商同学坐着与他交流,我则站在一边等待。但没想到的是,只在化妆室呆了一分多钟,商同学就有事要走,我理所当然的打算和他一起离开,但就在我们走到门口时,商同学在门口笑说既然我没事,可以留下来陪朱军聊一会儿,说完这句,他就先离开了。
我为什么会同意留在那间化妆室?因为当着朱军的面,我没有合适的拒绝理由、因为我需要采访他才能完成作业,也因为朱军是全国最有名的主持人、我们身处工作场合,我根本不觉得这会是一件危险的事。
在此之前,我从未在任何场合和朱军一对一说过话,交流仅限于在录制现场和其他人一起向他打招呼,我在实习时还看到过他的妻儿,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长辈。
于是我留在了化妆室,还想找机会采访他。但在一开始,朱军就主动向我提问,打过招呼后,他问我是不是老师带来的实习生,还告诉我他认识老师很多年,在她没结婚时就见过她的丈夫。
除了聊老师、学校,朱军还注意到我脖子上挂着一台索尼的微单相机,那是我为了拍摄找室友借来并随身携带的,因为那时微单还算少见,所以朱军还让我把微单取下来给他看,并拿在手里把玩了一阵,还用这部相机对着镜子给我和他拍了照片。有人故意在这件事上撒谎,说“笔录中显示,弦子还用自己的手机与朱军对着镜子合了个影。”明明是朱军拍摄了照片,笔录中也是明白如此。利用笔录不公开,移花接木,恶意制造这些虚假的信息。
一直到这里,我虽然比较紧张,但因为朱军随和松弛,甚至算得上亲切,所以我还在想接下来可以提出采访要求。
直到朱军主动问我是不是想要留在台里工作,他可以给帮忙,我才开始觉得奇怪:能留在央视工作非常难,我从没听说我的师哥师姐实习时能转正,更何况我的表现并不突出,他为什么要帮助我?我坦诚的告诉他我打算大四去考研,并不打算工作。朱军又开始告诉我他认识那所学校的校长,并且关系相当熟。
谈话到这里,我已经感到不安,为什么朱军一直主动对我提供资源与好处?不管留在台里还是考研,都是靠自己努力去做的事,尤其是考研要先通过专业课笔试,找校长有什么意义?我向来不喜这类人情世故,更何况接受朱军的帮助,我要用什么去回报呢。
朱军继续提到当时央视新楼已经建成,问我去过没有,说可以带我去,还说那附近有很多餐厅,可以带我去。他甚至还提到毕业之后我想要留在北京的话,也可以给我帮忙。我那时虽然只有大三,毫无社会经验,但总能察觉出他话语中对我们关系的设想是非常越界的,所以一直想要含混过去——如果我表现的对他的提议不屑一顾,那大概率会得罪到他,我只能委婉拒绝:我现在还是大三,想从事电影而不是电视行业,并不需要帮助。
朱军不理会我一直的否定态度,又说我的脸型像她太太,知道我是南方人后还说南方姑娘比较水灵。他拉着我的手要给我看手相,还告诉我根据手相来看我不应该靠近水——我是武汉人,几乎就是在长江边长大,这句话让我特别诧异且可笑,一直记到了今天。
在朱军拉住我的手后,我虽然在他说话时把手抽了回来,却并没有当场驳斥过他。
可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大三的实习生,我太害怕如果我不礼貌,就会得罪他,如果我得罪朱军,得罪这位艺术人生的主持人与总制片人,我就会被赶出实习组、失去完成期末作业的机会。在我们系,导创课作为核心课程,挂科有可能影响学位证,我大学的成绩一直都很好,四年没有挂过任何一门课,我根本无法想像我拿不到学位证会怎么样。所以即使是朱军不经过我的同意,拉着我的手要给我看手相,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我可以忍、我应该忍,为了我的学业,我不能够得罪他。
而当朱军开始对我有进一步举动,开始将手放在我的身体上,并隔着衣服猥亵我时,我则完全整个人都被震惊、恐惧紧紧攥住,陷入了应激状态,完全不知道怎么反应。
在朱军一开始让我把门关上的时候,我还下意识留了缝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在化妆室、会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直接碰我的身体。
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我,还没有展开过一段正式的恋爱,更何况是被一个年纪和我父亲一样的男性强迫触摸身体,甚至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性侵就是被陌生歹徒强暴、在公交地铁被咸猪手,我根本不知道女性可能被一个德高望重的名人、在工作的场合触碰身体。
在那样的时刻,我的大脑完全是一片空白的,能够想到的是我要让他停止,然而我能做的只是紧紧缩在椅子上。当他的手在我身上触摸时,我用胳膊挡开他的手、当他想要把我从椅子上拽向他时,紧紧的拉住我的椅子,不让我的身体离开椅子,因为那样我就会有更多的身体部位可能被他触摸。
我从未想过会被几乎陌生的男性触摸胸部、大腿,巨大的耻感在那时候笼罩着我,我害怕、想哭,但在那个瞬间的我,没办法想出任何对策。
为什么不对抗?可我不敢大声斥责他,因为我害怕被人听见、我也不敢反手去打他,因为我害怕他会对我使用暴力。我从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更何况一个比我年长、高大那么多的男性。
为什么不逃跑?可我太害怕,我担心如果朱军拉住我不让我离开怎么办?我应该挣脱?应该喊出来吗?可我不敢,我甚至害怕如果动静太大,我被别人看到朱军将手放在我的身上,那样会发生什么?我会不会被羞辱?这件事会不会被所有人知道?其他工作人员会怎么看我?一起实习的同学会怎么看我?如果闹大了,我们学校的师生又会如何看我?
“被性骚扰并不是受害者的错”这句话说出来简单,可对二十一岁的我来说,在那个化妆室被朱军触摸时,能感受到的就是巨大的耻辱、想要哭、想要把头埋进土里、想要一切都没发生过。
很多人造谣说,在性骚扰发生的过程中,有快十人、十几人进入过化妆室,然而这是彻底的造谣——在性骚扰发生的时候,化妆室进来的只有四人:跟随朱军多年的、两位分别姓李、张的制片、助理,和两位观众。
只有这四位,其他都是春秋笔法的造谣,在朱军断续实施猥亵行为的期间,没有其他人进入过化妆室。最后节目嘉宾带着人来,是我趁机摆脱朱军的机会,性骚扰的行为都发生在嘉宾进入化妆间之前。
我为什么不在这两位制片、助理进入化妆室的时候逃跑?因为即使我只来这里实习了几个月,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两位中年男性,是整个节目组里和朱军关系最紧密的人。
这两位制片人、助理,要和朱军一起出差、一起出席活动和饭局、要找朱军签合同与报销单、要传达完成朱军分配的工作。我见过他们沟通时的状态,我知道他们跟朱军的利益关系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作为节目组总制片的朱军,可以影响他们在台里的工作和发展。
对他们来说,我不过是一个最无足轻重的实习生,朱军则是他们的领导与利益共同体,如果我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我正在被性骚扰、如果我当着他们的面指责朱军,我能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我能想到是,他们可能会包庇朱军,让他继续伤害我。
他们自己进来的两次时间里,停留的时间都十分短暂,在那样短暂的时间里,性的耻感、对他们的不信任、害怕事情被闹大我被公开羞辱、害怕失去学业。所以,我不愿意让这两个中年男人知道朱军对我的意图。在他们进来时,我甚至深深的低下头,想让头发遮住我自己,不让他们看到我的表情,不给他们造谣中伤我的机会。
我没有对着朱军的工作人员呼救,并不意味着我不想反抗、停止朱军的性骚扰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已经用了所有我能够想到的方法让他停下:我用手推拒他、我试图和他沟通让他停止动作。
不一会儿,有两位观众敲门,请朱军签名,可我看到朱军站在门口,我那时太过恐惧慌乱,不敢走上前推开他离开化妆室。这个过程结束的非常快,我还没做好准备,那扇门就又被合上。在朱军试图继续时,我不得不重新坐回椅子上,因为我需要坐着,坐着身体展开的部分没有那么多,他也很难拉扯我。可他的行为还在不断升级,甚至强吻了我:这件事直到今天都在折磨着我,因为我不愿用这么美好的词描述他的行为,却也别无他法。
直到朱军试图把手伸进我的裙子时,我已经接近崩溃,浑身都在发抖——朱军看出了这一点,大概是终究怕我喊出来闹出来,他停手并沉着脸坐回椅子。那时候我手脚发软,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我并非不想离开,即使那时候的我已经完全处于应激状态里、想要痛哭却一直在发抖、喉咙颤抖就好像失声一样、满脑子都是羞耻与畏惧,然而即使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也没有放弃离开。幸运的是,节目嘉宾带着很多工作人员走进了化妆室,朱军站起身和他沟通。直到嘉宾进来和他交谈了一会儿,我大脑才渐渐恢复清醒,察觉到这是可以离开的机会,低着头往门口走——我以为朱军不会在嘉宾面前制止我,可时至今日,我还记得朱军看到我要走时说了一声“你要走啊?”,我愣住了,过了几秒才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要走。”
我对那句话印象那么深,是因为我无法相信,即使我表现的那么痛苦、那么抗拒,他依然觉得我应该留在那个地方,他如此蔑视我,以为我软弱且胆小,这种耻辱感直到今天还在折磨着我。
而我之所以只能在嘉宾来的时候离开,是因为我知道相比张、李两位朱军下属,这位嘉宾是节目组的外人,和朱军没有利益关系、甚至在演艺界的地位和朱军平起平坐,朱军会在意他的看法和对自己的评价。而且嘉宾自己的工作人员,对朱军来说也是不可控的存在,即使他们不会帮助我,但朱军在他们面前也要注意举止,否则总会有传言流出。
所以,在嘉宾进来之后,虽然我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说出我的遭遇,我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逃了出去。
2.
在之前我就说过,2018年我写下长文时,原因只是我的一位姐姐公开了自己读书、工作时被性侵的经历,在看到姐姐的自述后,我就留言告诉她,我会把我的经历也写出来——我希望让她知道,她的勇气是有意义的,我会传递下去。
那天,我只是想写下我的经历,安慰姐姐,也告诉我认识的女生,被伤害不是我们的错。在写下那篇记录时,已经距离报案过去四年,因为我报案从未得到过书面材料,所以我也缺少依据来确认回忆的全部细节,我将那位匆匆一瞥的中年歌唱家嘉宾,误写成了阎维文老师,直到去年庭前会议看到笔录,才确认其实那天进入化妆室,让我找到机会离开的其实是郁钧剑老师。
我一直想要为这件事带给阎维文老师的麻烦公开道歉,因为我在文章中确实记错了。时隔四年,记忆错误。而我当年在派出所的笔录中说的,就是郁钧剑老师。在此对阎维文老师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对郁钧剑老师表达迟到六年的感谢——您不知道,您无意中挽救了一个女孩,让她免于在不知所措中被继续伤害。
从我被商同学带进化妆室(18时12分6秒),到我独自在楼道并神情低落的用纸巾擦嘴(18时57分17秒),这是我在化妆室的全部时间。而这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是一开始朱军和我的沟通交流,并不是性骚扰发生的全部时间。
在性骚扰的过程中,也根本没有近十人走进化妆室我却任由性骚扰继续发生的情况——我已经说出了化妆室的全部经过,我为什么在李、张二人与观众这三次进入化妆室时不逃跑,而是等到嘉宾进入化妆室才找机会离开。
在离开那间化妆室后,我给我的姑姑打了电话,姑姑要我忍下来,我回学校告诉了室友,室友也要我忍下来,她们要我为了学业沉默,于是我甚至在第二天又重新回去实习。
但当回到性骚扰发生的空间、看到节目组的员工、看到带我去化妆室的实习生、看到那间化妆室时,恐惧与耻辱才终于逐渐变为愤怒。我意识到继续待在这个空间、继续实习带给我的折磨实在太大了,一想到自己还有可能再次陷入那种处境,我就觉得自己宁可死去。
我一个一个的打电话,可无论高中还是大学好友都要我忍气吞声,直到我终于找到另一位大学老师,她是第一个告诉我要报警的人,也是在后来陪我报警、保护我让我学业不至于被打击报复的人。
3.
在我二十一岁,一个人躲在走廊一次次打电话时,或许那时心里想的是痛苦与折磨,但总有一点微弱的勇气,在告诉我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我值得一个正义的对待。这微弱的勇气支持着我继续,直到终于有人告诉我应该报警。
2014年6月10日,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派出所、第一次做笔录时,我忍住痛苦与耻感,不得不详细描述在那个化妆室发生的一切,尽力诚实而有尊严的保护自己。可我没有想到,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记录,却会被曲解成“被摸了四五十分钟、有近十人进来还不跑”的故事。
我没有想到,当年那个痛苦又慌张、二十一岁的我,会被那么多人指责“编色情小说”、“那么多人来都不跑就是在迎合”、“摸四十分钟没有被摸破皮吗”、“你的脸和身材值得被摸那么久”、“一男一女那么长时间怎么可能只是摸”、“十几个人进来你不会跑吗”……
在那些嘲笑声中,什么样的受害者才可以被称为完美呢?在封闭空间提前预料到性骚扰并录音录像?在被侵害的时候激烈搏斗留下证据?在事发后立即报警公开并寻死觅活?
可对二十一岁的我来说,我没有预料到化妆室会发生性骚扰所以我没能录音录像、我害怕得罪朱军会影响学业所以不敢搏斗、我担心别人会包庇他的作为所以不敢求助、我知道嘉宾与朱军不存在利益关系所以逃脱、我太过害怕所以在第一天不敢声张、我得到鼓励终于去报警——所有这些过程对于二十一岁的我来说就是自然发生的,我的害怕与勇敢都是我的一部分。
我相信有过同样感受的女性一定能体会我当时的恐惧。关于封闭空间里,身体被侵犯的羞耻经历,被那么多人施加色情与戏谑的想像,无论我多么不愿意承认这耻感,也要说我确实会被击溃。我不愿去想有多少人将我在那个化妆室的屈辱经历扭曲成色情小说一样的意淫段子——女性被性骚扰是色情小说吗,为什么我的眼泪会成为其他人的笑料呢?
从14年到如今,6年的时间里,我对那个封闭空间遭遇的被侵害经历始终诚实,这就是我保护自己尊严的方式,也已经是我竭尽全力所能做到的完美。
我在2014年就已经尽快报案并全力配合了调查,在四年后站出来,从未故意撒谎、隐瞒任何事。我当初的畏惧与勇敢是证据,身体被侮辱的经历与随之而来的耻感是证据。即使这意味着我要在所有人面前详细的回忆我的人格与身体被侵犯的细节,让我再次因此备受折磨,这痛苦也是我的证据。
以上,是我在六年之后,终于向公众作出的公开“笔录”。是发生在我身体上的经历,是我的痛苦与耻辱。我会在接下来公开更多相关信息,让大家看到这两年来我经历的、我正在经历的。我对我所说的一切负责。
从始至终,我会用我的软弱与勇敢,用我的诚实与痛苦,来提出我的问题,来寻找我的答案。
(责任编辑: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