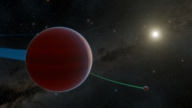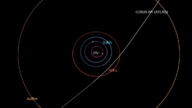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大纪元获得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该书部分内容。本文为第十二部分:在打手面前睡着了。
(编者按:大纪元获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高智晟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的部分内容。这本书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师在整个十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历的酷刑、牢狱生活、军营武警的暴虐、最高层的胆小如鼠等鲜为人知的内幕。高智晟律师承受了地狱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监狱,并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虚弱、腐烂和崩亡。)
中共从2006年迄今,对我数次施以酷刑,一、必须改变身份,哪怕是形式上的;二、抹灭关于酷刑的文字;三、最后一次的强迫下跪。最后那点上使它得以遂愿?他们的一位正团级干部给我谈及我付出的代价时说:“我们看得是心惊肉跳,那付出的代价太吓人了。”他跟我谈到这种代价与中国进步事业前景的关系时(现在不便特别清晰地说出他的身份,担心给他造成伤害),我说我认为,我的这种坚持并无多少宏大愿景及价值的支持,也算是我的一点倔强吧,大家都是人,凭什么我就必须俯伏在你的价值之下?是你持有的价值本身?还是你的德性和才能?靠着电击器、靠着凶残来聚拢并维持“支持”,那本身即是一种自我否定。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你野蛮强权逾越不了的障碍。这不是口号,这是我们冲突十年的结果。强权使遍解数,没有改变我,作为他们认为的障碍,我还存在着,不客气地说,还依然有着力量,当局迄今不舍昼夜地动用大量人员围在我的周围就是个证据。
而这是最后一次的肉体酷刑过程,从他们向上面汇报的画面上看,我肯定是“下跪”来的,但美中不足的是,“重八君”压着我的双肩,而“阿巨兄”则踩在我的两只小腿胫上,除非“领导同志”们脑子里灌进了猪尿,否则,瞄上一眼,即可以看出那外力作用下下跪的虚假。
回到房间,王处长又旧账重翻,还是让我口头说一遍2007年那个文字记述的酷刑是虚假的,但终于还是没有实现这一大愿望,虽然为此又颇下了些野蛮的功夫,我在惨叫声中他们气喘吁吁,结果还是不那么完美。王处长等三人累了,已经是深夜了,当天夜里的酷刑,就目的而言是个无果而终的结果。
他们有一个人走了出去,不一会又进来两个新的面孔,王处长走出了门,“重八君”来了一句,“孙子,你这几位大爷累啦,回去休息,由别的大爷陪你玩,慢慢儿熬着吧孙子”,然后也走出了门。前面王处长说过是来了多位大爷来伺候我,因为这时我是躺在床上的,我并未抬头看来人。
由于我是切断了思维活动中,这最大的好处即是但得暇隙即会有睡意强势光顾。我听到有人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头跟前,我睁眼一看,一只穿着皮鞋的脚就搁在我的鼻子跟前,不到两分钟,我就睡得稀里糊涂,大约是那扯鼾声太没有顾忌场合,头上被人踢了两脚。用力倒不大,随即骂声赐下“妈的X,你丫的真的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东西,连这环境你都能这么快就睡着?”实在不敢恭维,那声音绝对是娘娘腔。我这里绝无性别不敬的意思,女性的声音是女性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但那美的女声若为一个男人拥有,那实在别扭得可观。迷迷糊糊,不到两分钟,我又酣然入睡,我又被踢醒,娘娘腔又把骂声赐下“高智晟,你丫的傻逼呀,你丫的真的没肝没肺呀,今儿是什么动静,你居然能睡着?你丫的不是傻逼是啥?”显然,这娘娘腔跟我的睡觉干上了,骂声还是在继续,“这什么场合?丫的都能睡着?大爷们在隔壁听了,大概几天都睡不好,说你畜生畜生的,你丫的真不是人呀?”他说着说着,我的鼾声又吼了起来,其实,我平时睡觉很少打呼噜的,只有仰面朝上的姿势且不枕枕头时才会鼾声大作。那天,王他们离开时,将我的手拷在了前面,并用我的腰带将我的两只手绑在小腹处,我仰面一躺即鼾声骤作。
我有若干种迅速入睡的本领,这是我在前面几年的律师生涯中历练出来的。有时庭审休息十分钟,我即可成功地睡上六七分钟,这实际上是我在学着控制自己情绪时的一个意外收获。我控制情绪的方法即是用意念闸断情绪,将之骤然用意识凝固,颇成功,可出现了别一个趣获,即不出两分钟,即会意识混沌,稍作纵驰既可立即入睡,这点意外的收获,在这十年里使我大受其益。便是在酷刑闲暇,打手们休息一会,我就能获得实质性的休息。不论什么过程中只要眼前出现了一点可供休息的时间,我会立即利用起来,因为这十年的经历太特殊,我的所有时间都成了中共特务们的支配物,许多特殊过程中,没有任何规律及经验可循,最明智的做法即是见缝插针,有时间“到手”即立即入睡。因为像2007年时曾有整夜整夜不准你入睡的情形,他们两小时一轮换地坐你面前不准你睡觉,这种事,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
不是今天回头才意识到,即便在当时,我已经觉察到,当对方不能改变我的身份时,他们会把眼光投向我的身体健康,干预人的健康,若不借外力来实现诸如药物、细菌等,剩下的只有食、睡两样关键的过程。而他们能掌持的则只有食一样东西。而食对于人的健康影响的功能有限,除非他们刻意地量控,像在2007年9月时的故意饿你。否则,食物质量对人健康的影响效果完全取决于精神因素,实际上就是人的心情。我曾与当局谈话人提到过,想用饭菜质量达到损害我健康的目的,无异于拿着牙签刺激太平洋,是在做滑稽的无用功。
这几年我获得一个很有价值的宝贵经验,那就是在任何困难的过程中,或者是应对任何困难,你需要的就是持续地培蓄自己的精神规模及质量,使精神无限强大起来。强大的精神几近能给处在物质极度困乏过程中的人提供无限的支持。我这十年的经历可完全现实地证实这一结论的正确。
当局这十年来,在对我的囚禁及食用计算上,可谓用心至其极,尤以部队的二十一个月囚禁及沙雅监狱的三年囚禁为甚,一口气禁闭式囚禁三年,一口气吃三年的煮白菜,除减少了三十多斤体重外,当局一无所获(有趣的是从沙雅监狱出来被当局押回家仍被软禁着,不到四十天的时间即增加了三十多斤的体重,不知研究对付我的专家们有何感想了。
我的睡觉不仅迅捷,而且颇坚韧,一般的捣乱效果不彰。根据我的经验,施行酷刑的人休息后换进来的人就是看管人员,但一般酷刑期间安排的看管人员都坏得可以。那晚的剩下的几个小时里,我就顽强地在顽强的干扰中睡得五迷六倒,那实在是太累了。
正如所料,接下来的几天里,疾风暴雨式的肉体酷刑已经停止,换来的是近乎和风细雨的以疲劳肉体为目的手段。那种设计过程也足够绵密毒辣,也足够的难熬。他们分为三班看管我,每班两个人,所谓的“三包一”模式,即有三个班车轮式轮流地看管同一个目标。那绝对是一种蓄意的安排,每个班上都由一个绝色的坏种负责。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领导具体安排,能够自觉能动地做恶且不知疲倦。接下来的几天由他们看管真给我制造了些苦楚。
对于这些苦楚我不打算在这里细述,加上我在那几天里思维基本上处于一种混沌状态。首先是我基本不自觉地启动思维,使思维呈自然的休眠状态,使人的所有痛苦局限在生理方面,即使是在生理方面,这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稀释了痛苦的被注意程度。经历过酷刑的人都当记忆尤深,酷刑创制的真正痛苦除了电击外,当在酷刑停止后的五天内,尤以前三天为甚。那是所有生理痛苦的集中聚拢时段,分散注意力是减轻痛苦的不二途径,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看,莫过于遏制思维运动。而对思维的着力遏制的一个显着收获是没完没了的睡意。
我整天处在昏睡或半昏睡状态中,绝不是夸张。便是在强制站立阶段,我亦可迅速地进入迷糊乃至酣睡境,美中常有不足,每至酣睡境,膝盖就会猛地打屈,招致看管人员的几脚猛踹,终于不能阻绝那更强悍的睡意,这实际上也不当全然归责于我,实在是因为那近乎理想的足使人昏睡的环境。切断思维是一个方面,另外两个利睡得绝好因素是近乎死寂的安静和大白天在房间里给你戴个黑头套。那个过程,睡能让人幸福得昏昏噩噩。三个绝好的睡眠条件他们就给了两个,你是不想幸福也不行。#
附:高智晟新书订购链接
https://www.amazon.com/dp/B01JTGUFU0/ (电子版)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55(精装)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48(平装)
(转自大纪元,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归高智晟及其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