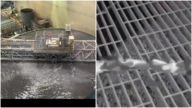该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1967年1月初,当时权力问题浮上台面。毛氏中央知道,与前领导人刘氏的对抗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后者在北京处于困境,但在大多数省份仍然能依靠强大的盟友。为了决定性地将它消灭,造反派不得不夺取政权。由于作为比赛主要参与者的军队坚决拒绝介入,显然主席的新部队将拥有所需的一切回旋余地。上海在1月份发出了第一个信号。很快,所有市政当局和党委都被推翻了。突然间,造反派再也不能仅仅在场外批评,而是不得不承担执政的任务。因此,灾难开始了:造反派中敌对团体之间、学生与工人之间、长期合同工与按日计酬的散工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这些紧张关系迅速演变成涉及整座城市的重大对抗,然后升级为使用枪支和刀具的肉搏战。此时如此接近夺权的毛派领导人突然对此大吃一惊:工业生产正在崩溃(1月武汉下降49%),政府管理部门正在瓦解,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开始夺权。中国正遭受严重缺乏胜任干部的困扰,因此造反派别无选择,只能让大多数受打击者复职。工厂的生产必须恢复,教育机构不能无限期地关闭。因此,在1月底,领导层做出了两项决定:建立一个由革命委员会组成的新的权力结构,基于“三合一”即造反派、前干部和解放军之间的联盟的原则;让红卫兵悄然退出(或回到教室),如果必要的话,利用毛的其它武器──已处于警戒状态6个月的军队本身。
当时,向中央靠拢并不是对造反派的保护,文革还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到来。4月恢复正常化进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毛感到忧心。在所有地方,保守派和1月份被淘汰出局的人再次抬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与解放军成立了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联盟。武汉就是这种情况,那里造反派正在撤退。因此,再次迅速向左转的时候到了。7月中央文革小组在两天之内逮捕了武汉军事领导人,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正如每当毛派红卫兵认为情况进展顺利时所发生的那样,这种转变引发了近乎无政府状态的暴力和派系斗争,使革命委员会在某些地方的成立变得不可能。结果,9月,解放军被授权使用其武器(在此之前,它被迫袖手旁观,看着其武器库被抢掠)。此举为造反派提供了新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1968年是1967年的重演。3月,毛再次忧心忡忡,并再次向左转,但较为温和。对抗变得越来越血腥,造反派在7月被彻底粉碎。
因此,在毛发现自己面临着残酷和不可避免的两难困境──左边是混乱、右边是秩序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犹豫不决。所有演员都在期待这位导演的下一步行动,希望这对他们有利。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不共戴天的敌人都依赖于同一个活着的神。因此,例如,当强大的保守派武汉“百万雄狮”联盟在1967年7月得知事情不会按正确的方向发展时,它宣称“无论我们是否信服,我们都必须遵循并实施中央的决定,没有任何保留”,并立即解散。由于对毛泽东所说的从来没有明确的解释,那些可能被认为处于权威地位者──党委──实际上几乎不受注意。由于人们发现难以相信毛本人可能如此优柔寡断,关于中央的真实意图也众说纷纭,混乱盛行。钟摆的摆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快每个人都要求进行某种复仇,而当下获胜的一方绝不会宽宏大量。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外,两个内部因素在加剧暴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造反派组织内部。从未被以民主方式仲裁的小团体的利益和个人的野心,不断导致党内新的分裂。而愤世嫉俗的“政治企业家”试图通过结交新的地方势力,特别是培养与解放军地区总部的密切关系,来改善自己的地位。许多人最终与四人帮建立了密切联系,且实际上成为省级独裁者。渐渐地,派系斗争失去了其政治性,变成了身居高位者与想要取代他们的人之间赤裸裸的权斗。和劳改一样,任何提出指控的人总是对的,因为这些指控伴随着一连串的引用语和极神圣的口号。一般来说,那些试图为自己辩护的人结果总是陷入更深的困境。唯一有效的反击是在更高层级进行反诉。指控是否有任何依据,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要以正确的政治术语被表达出来。在此逻辑下,辩论导致战场不断扩大、树敌不断增多。归根结底,由于一切都是政治性的,最微小的事件都可能被过度解释为最恶劣犯罪意图的证据。结果就是通过肉体消灭进行仲裁。
这些事件可以称为内战而不是大屠杀,尽管内战几乎自动地导致大屠杀。这越来越成为一场涉及每个人的战争。在武汉,1966年12月底,造反派监禁了3,100名干部和保守派。造反派与“百万雄狮”冲突中的首例死亡发生在1967年5月27日。结果,战略要点的武装据点被占领。造反派各总部于6月17日被查封,有25人死亡。截至6月30日,伤亡人数上升至158人。在失败后,600名保守派被杀,另有66,000人遭受了这种或那种迫害。在1968年3月向左转的那一刻,追捕陡然加剧。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在一座体育场内,日益受暴徒控制的民兵组织在街头散播恐慌,武器从邻近省份涌入。5月,造反派派系间的战斗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内战再次发生。5月27日,一天之内军中就有8万件武器被盗。这是一项新纪录。一个真正的、武装起来的黑市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工厂甚至开始为造反派不同的派别生产坦克和爆炸物。截至6月中旬,已有57人被流弹击中身亡。商店被洗劫一空,银行被劫掠,人口开始逃离该市。但就像某种扭转乾坤的力量一样,来自北京的一份声明挽救了这一天,导致造反派垮台。解放军于7月22日进行了干预,未发一颗子弹就掌握了控制权,各派于9月被迫解散。在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比如福建,相较于城乡之间的古老差异,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分裂程度较低。当来自厦门的红卫兵抵达省会时,遭到了人们的抨击。他们喊道:“福州属于福州本地人……福州人,不要忘记你们的祖先!我们将永远是厦门人的死敌!”在上海,真正的冲突存在于苏南人和苏北人之间,但不是那么直接。甚至在长弓这一很小的地方层级也几乎可以看出,革命派系间的斗争是昔日纷争的重演,涉及统治该村北边的陆氏家族与统治南边的沈氏家族。这也是算旧账的时刻。这些旧账包括一系列纷争,可追溯到日本占领时期或1946年土改的血腥开端。在颇具乡村风味的广西地区,被赶出桂林的保守派逐步用农民民兵包围了该市,并最终取得了胜利。1967年7月和8月在广州,红旗与东风组织各派之间的激战导致900人死亡。一些战斗甚至动用了大炮。
在此期间情况实际上有多恶劣,可从当时一名14岁红卫兵的如下言论来判定:“当时,我们还年轻。我们很狂热。我们以为,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只有他才掌握真理,他就是真理。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我相信,文革有充分的理由。我们认为我们是革命者,因为我们是听从毛指令的革命者,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解决一切,解决我们社会的一切问题。”暴行变得越来越普遍,且具有比前一年更“传统”的特性。有人在甘肃兰州附近目睹了以下事件:“肯定有大约50辆车……每一辆都有一具尸体捆绑在散热器上。一些卡车捆绑着不止一具尸体。它们都沿对角线直挺挺地躺着,并被用绳子和金属丝绑在那里……人群围着一名男子,用矛和粗制的剑戳他,直到他倒在地上,躺在那儿,成了一大堆血肉。”
1968年下半年,军队重新掌握了控制权,并加强了控制。红卫兵被解散。那年秋季,数百万年轻人(到1970年,总数为540万)被发配到乡下,希望将留在那儿。许多人待了10年或更长时间。在毛死之前,有1,200万到2,000万人被以这种方式强行农村化,包括来自上海的100万人──占该市人口的18%。300万名被撤职的干部被发配(往往是几年时间)到五七干校。这些学校名义上是训诫中心,实际上却是监狱。毫无疑问,这是屠杀规模最大的一年,因为工人团体和士兵夺回了南方地区各校园和城市。广西梧州被用重型火炮和凝固汽油弹所摧毁。在一场真正的战役之后,桂林于8月19日被3万名士兵和武装农民所攻占。在这场战役中,政治和军事团队设法将农村居民对文革的漠然煽动成积极的敌意。造反派被集体处决了长达6天。收复桂林一个月后,恐怖蔓延农村,这一次针对的是“黑类”和国民党。他们是永恒的替罪羊。它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最终一些地区可能吹嘘它们“完全没有了黑五类中任何一类的任何成员”。正是在那时,共产党的未来主席、负责其所在省安全的华国锋,赢得了“湖南屠夫”的称号。该国南部受害最深:广西或有10万人死亡,广东或有4万,云南或有3万。红卫兵极其残忍,但最严重的暴行却是由其刽子手即执行党的命令的士兵和民兵所实施的。(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