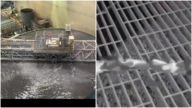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2月17日讯】我不是什么乐迷,一般歌星离开了,我不会主动对其作出任何报导或评价,正如比凤飞飞“早走一天”的“美国天后”惠妮•侯斯顿突然在洛杉矶去世那样,反应是有的,但不会太大。但是,凤飞飞的离去,却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因为,在我的青春时代,是听着她和当时不少台湾歌星的歌成长的。
那是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时期。
其时,我和许多来同样自广州的知青下乡至光明农场。农场位于宝安县(即今日深圳光明新区),因此,只要有收音机,即使是“原子粒”(即半导体),就可以收听到香港的电台节目。不过,那时公开收听是不可能的,只能偷偷地听。当时文革还没结束——那怕不是因为文革,也因为要坚持阶级斗争,凡偷听境外广播的都属“收听反动电台”,一旦被揭发,至少会被列入批斗行列。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常常偷偷地“收听反动电台”——香港商业电台(下称商台)。每到深夜时分,就会有音乐节目,播出的歌曲绝大部分为国语流行歌;到了下午两三点时间,则有“点唱歌曲”节目,所播出的歌曲也大多为国语流行歌曲(到港后才知道,整个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雄霸了香港乃至东南亚华人社区,粤语流行歌是自1973年电视剧《啼笑因缘》的同名粤语主题歌播出后才渐渐成了香港流行音乐的主流)。那时的下乡生涯无疑艰辛的,幸而整个生产队(100多人)都是广州不同学校的知青,尽管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可是,因为都是来自广州,彼此的习性特别是因为广州的特殊位置所造成的文化背景,例如,广州过半家庭都有海外港澳关系;再如,我家中有唱机,甚至有来自香港当时最新的粉红色塑胶流行音乐唱片,别的同学家里也有类似情况:嘴嚼巧克力不是新么新鲜事,由父母带着到太平馆吃西餐也非罕见。1960年代初期,当时《羊城晚报》每逢星期二有半版港澳新闻、市民可以看到香港电影(尤其是粤语片)——这都是在当时内地别的城市所没有的。故而,来自广州的这一群“学生哥”听听“反动电台”里面的歌,成了很自然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在那个时候,白天“唱红歌”,晚上听“黑歌”甚至还会哼唱“黑歌”就成了现在看来构成极大反差的荒诞感。
一次,一个同学从宿舍走出来时不经意地唱《何日君再来》,殊料被指导员(是个复员军人)听个正着,当时指导员只说“有那么多歌唱,为什么要唱这歌?”不料到了晚上召开全队会议,要批判这个同学。同学交代说,是从商台学回来的,唱歌的人是叫凤飞飞!随即,他进行自我批评并要他交出自己的收音机了事。
其实,对我们知青来说,凤飞飞、尤雅、姚苏蓉、崔苔菁、包娜娜、青山、赵雷、鲍立、林冲等这些台湾歌星都是熟知的名字,较流行的就有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南屏晚钟》,至今我们还可以熟练地唱出《绿岛小夜曲》: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当时在我们听来,凤飞飞的歌声格外柔软,像是轻巧地湖面上绽开的涟漪,一圈又一圈的波潾,让人着迷。
不久,一些有较好音乐基础的同学根据听回来的记忆,将这些“反动电台”歌曲记下了简谱,填上歌词,还写上原唱者是谁。很快地,这些手抄歌谱就传了开去,厚厚的一本又一本,流行歌就这样流传了开来。有时,男生更会对着女生大唱凤飞飞的《姑娘十八一朵花》:“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眉毛弯弯眼睛大,眼睛大;红红的嘴唇雪白牙,雪白牙;粉色的笑脸,粉色笑脸赛晚霞,啊!姑娘十八一朵花,一朵花!”
无论在物质或精神上空前匮乏的年代,尽管对香港流行文化相对并不截然陌生的广州知青,也急需找到因为生活在不属于他们却需要流汗甚至流血的地方而遭遇困惑、迷茫和失落的情绪宣泄,何以解愁?唯有利用看不见的电波掬取一些令他们可以稍感舒畅的柔性乐章,按摩一下疲惫的心灵。凤飞飞,就成了知青们其中所要掬的一朵云彩或一抹彩霞。
文章来源:《网易》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