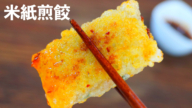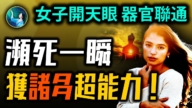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12月29日讯】 一
十八大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新的中共最高当局——七位政治局常委——仍处在兴奋紧张的接班过程之中。其中,习近平、王岐山、刘云山三人已经基本进入角色,并展现出了与其前任略有不同的政治形象:说了一些有所不同的话语,作了一些有所不同的姿态,传达了一些有所不同的信息,虽然不同之处并不显着,还只是若隐若现,微露端倪。
习、刘、王三人的接班速度比人们预想的要快一些。这首先应该归功于胡锦涛“裸退”之“高风亮节”(胡锦涛仍有国家主席一职尚未交卸,但该职务为名誉性虚衔,除外交场合有所不便,并不影响习近平在新班子里的地位和实权),以及“胡锦涛Style”之政治魅力和人格魅力的极度缺乏,以至于“人一走,茶就凉”,十年辛苦集聚的政治影响力几乎瞬间消散于无形;其次也应该归功于李长春、贺国强不仅“裸退”,而且似乎已经“全休”。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但应该做的事情真做了,在中共也不容易。
至于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四人,目前还只是登台亮相,尚未各就各位,仍处于接班之前的见习期。此四人需等到明年“两会”之后才能获得与其各自的党内分工相适配的党外正式职务——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和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获得这些正式职务之前,他们的常委身份并无足够的实权支撑,相当于只有爵位而无领地的贵族头衔。
从十八大到明年“两会”,这是一段新旧交织的过渡阶段,会出现诸多名实不相符、权责不对应的状况。到明年“两会”结束,这场十年一度的高层交接班大戏才告落幕,各省、部、委的职权瓜分火拼也才能基本平息。要问权力交接是否顺利、是否成功,新班子是否有能力稳住阵脚、开创新局,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够下初步的结论。
二
在中国古代,来日无多的老皇帝为了给他将要继位的儿子创造政治机遇,有时会故意设局,将忠诚能干的文臣武将投闲置散,将腐败堕落的贪官污吏不予惩办,将众所周知的冤假错案拒不平反,将万众期盼的改革政策留中不发,这是为了让他的儿子可以迅速地找到正确的施恩对象和适当的发威机会,以便甫一继位即有所作为,一展圣明君主的风采。把好事留给后任去做,不惜以自己的恶名去衬托继位者的美名,这是专制皇权时代树立新君权威的通幽曲径,胡锦涛之于习近平,当然没有如此体贴的用心。不过,以客观效果论,则情形极其相似:胡锦涛的僵化和平庸,胡温体制对改革的冷漠,对腐败的放任,的确给习近平、李克强们人为创设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性机遇。
十年来,胡锦涛抵住国内外压力硬是不平反“六四”,不推进非毛化,不摒弃以言治罪,反而强行重判了刘晓波;而许多早就该做、且并不难做的政策性改变,比如废除劳教、制止强拆、改革户口制度、实行阳光财产法案、约束城管恶政、惩治截访暴政、修正计生政策等等,胡锦涛明知在这些事情上舆论滔滔、民意鼎沸,却就是强装不知;明知这些事情利国利民、大有可为,却就是坚决不为。此类悖民意、逆公德的颟顸昏庸行径给习近平的任期留下了广阔的改革空间,足以让新班子如行云流水一般做出一番“习李新政”的阵势来。
实在说来,有胡锦涛时代当陪衬、作对比,习近平很容易出彩。人们久已厌倦了思路狭隘、言词乏味、形象呆板、表情木讷的“胡锦涛Style”,习近平只需稍显“新派”,略表“新意”,就足以让很多党员、很多国民产生“新风扑面”之感。
新班子登台亮相以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刘云山诸人相继表态要深化改革,要强化反腐,要从政治局做起改变“会风”、“文风”、“作风”(开短会、讲短话,不讲空话套话,座谈会不许念讲稿,汇报会、研讨会不要先“定调”,出行要轻车简从,不封路、不扰民),等等,此类言行立刻在民间引起广泛的好感。包括一向为人诟病的意识形态和宣传主管刘云山,也因在会议上公开引用李瑞环所说的“空话套话连野猪都骗不了”的故事而获得舆论好评。刘云山短短一席话使得其早已定型的“五毛党总书记”丑陋形象大为改观,足见中国人民对愿意痛改前非的当权者其实很宽容。真心推动政改者将会得到人民的厚待,即使他曾经犯过严重的过错。
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习近平及其新班子的好感并非因为他们的表现优异。习近平的确显得比胡锦涛更平实、更自信、更从容,但也仅此而已,习的既往政绩不足称道,常委生涯乏善可陈。归根到底,人们对习的好感其实全拜胡锦涛所赐。那些新意不多的所谓新话语、新作风之所以仍然能够显得新鲜、获得好评,皆因有胡锦涛先生沉闷僵化的旧话语、旧作风作为反面教材。忍受“胡锦涛Style”达十年之久,人们乐于见到一些“非胡化”,仅此而已。
三
无论如何,在高层大换班之后,中国的政局必会发生一些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变化,这几乎是一个确定性的事情。这并不取决于习近平、李克强是不是真正的改革派,甚至也不取决于政治局常委以及政治局中有几个改革派、几个顽固派、谁比谁厉害。政局变化的确定性首先在于极度腐败的中国政体滋生并积累了太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必须有所改变、否则难免崩溃的政治社会局面;其次在于胡温“黄金十年”在政治上实在是过于平庸,几乎无所建树,胡锦涛的政治宝库里并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供其接班人传承,他的后继者既不值得、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在他的阴影里原地原样坚守。
中国政局的变化要么产生于改革,要么产生于不改革。形势比人强,不变也得变。当然,好的变化只可能来源于好的改革,而不好的变化则各有各的来路。
仅仅在姿态、话语、“会风”、“作风”上做一些无伤大雅的“非胡化”改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就开始谈论“习李新政”,妄断此一“新政”的方向、目标、内涵和品质,更是言之过早——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
十年前,我们很多人曾经真诚期盼“胡温新政”,那确实有点儿幼稚,但也并非纯属一厢情愿。那一年“非典”来袭,人心惶惶,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两位部级高官因向公众隐瞒疫情而被胡温革职。隐瞒灾情、疫情在中国并不稀罕,本是中共一党专政多年养成的恶习,张、孟依惯例行事却不幸中枪落马,自然是可以被理解为“新政”的。广州的收容所里打死了无辜的大学生,导致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重庆的农妇拦住温家宝大诉讨薪之苦,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声援农民工讨薪运动——这些事情,也都曾被泛泛理解为“胡温新政”。
当年,胡温政府若真心诚意实施新政,新政并非不可为——只要继续沿着罢免张孟、废除收容的路子往前走,朝着人权、法治、公开、公正的目标往前走,新政不是镜花水月。然而,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新政只是仓促之间开了个头,后来就再无下文。现在想起来,所谓“胡温新政”更像是一个骗局,像是庸碌政客匆匆履新时的道德伪装,是权位不固、立足未稳之际哗众取宠换取民意支持的权宜之举。胡温十年,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而政治改革几无寸进,甚至连这个名词后来也遭到了官话体系的排斥。政府越来越腐败,官场越来越流氓化、黑恶化,比张文康、孟学农恶劣百倍却越坏越升官的党政要员越来越多,比收容、欠薪毫不逊色的恶法劣行也越来越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维稳”机关越来越粗野霸道、无法无天——“胡温新政”终于无地自容、无计可施、无声无息、无疾而终。
正是在“胡温新政”大开倒车之际,借力于广大民众对官场腐败、豪强黑恶的普遍痛恨,薄熙来从胡温手里抢走了新政话语权,与王立军一道创建了属于他自己的新政品牌:“重庆模式”。而那一场以“唱红打黑”闻名中外的“重庆新政”,不过是一场以“黑打”取悦民粹、以“唱红”回归毛左的小规模文革复辟。“薄王事件”中央就没有责任、不需反思吗?是中央的改革派公然作伪,才引来地方的文革派大胆偷袭。
我们当然希望刚刚上台的新一届中共当局发动一场货真价实的“习李新政”,希望中国政局向着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的方向良性演变,但历史的经验表明,说新话、刮新风者所在多有,无非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而行新政者太少,改新政体者少之又少。上一个十年里上过了“胡温新政”的当,我们必须对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习李新政”更严格、更苛刻一些。对于政府,人民越挑剔,“新政”越有戏。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