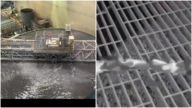残秋,清冷的晨光,我开了台灯,坐在书桌前。见窗外的长风吹落满树潇潇落叶.绿绒绒的草坪上落满了湿湿的黄叶,一片一片,无数的多.那么多感伤的灵魂,自枝头坠到滞湿的尘埃里.若盆景似的梧桐树,绿色的叶子先变成青色,一点一点地黄,一点一点自枝头剥落.阴润的天色里,树枝犹如满树繁花.有一种楮色的温柔、平定。
秋一深,人的味觉似乎也随着季节逆转了。我在电脑前磨蹭许久,翻翻书,写几行注定要删成白茫茫一片的文字。去厨房里熬了薏仁糯米粥。点了灶火,冰箱的冷冻室里拖出冰霜裹着的腌腊鱼.斩好,放进热油里头煎。雪白的豆腐煨在砂锅煲里,择净的金针菇、青蒜苗,一样一样地下到锅里,小火慢慢地煨煮。我立在灶前,守着锅,出神地看着楼下一树繁花的梧桐,枝上青的叶子,黄的叶子,似青似黄的叶子.咸鱼香里飘出清新的菜蔬气息,浓郁地壅塞在小小的厨房里。这是埋藏在时光深处的气味,腊鱼和青蒜苗的香味,是围着堂屋的火堆等待大雪来到的气息。故乡冬月的味道。天寒白屋,柴门犬吠,青翠的菜畦间落满了白霜。祖父为我留下的一枚黄柚,自枝头摘下,轻轻地放进厢房的青瓷小坛里……
咸香的腊鱼,紫殷殷的菜苔,稠热的白米粥,残秋冷雨,适合喝奶茶,金黄的红茶,热气腾腾的,兑滚烫的牛奶。冷雨天,心与人世亦起了隔绝,仿佛是襁褓里的婴孩,独自儿,在团团的棉花被子里,包包好。我决心做一个大雪封门的人,下雪也不出门。等来年春天再出门。
写字到深夜,照例踱到阳台上,撩开深垂的窗帘,透口气。寒气逼人的霜风,一阵阵地拂面吹过,在纯青夜色里穿曳。不再落雨,夜风将天空吹透了,是晶灿灿的星空,明莹寒澈的月光遍布穹隆与大地。天的东方有两三颗晶澈发光的启明星,一耀一耀地闪着光,它们告诉我说,天亮啦!天就要亮啦。
寒风里有轻轻说话的声音,有急急的脚步在纷纷地走过踏过,看不见人影。或者是魂灵在赶路也是说不定的。这深秋夜,仿佛有千年旧时光,自时光的罅隙间,泄一丝当年夜色,与今夜重叠。
那些温情传奇的前朝的夜色,当如今夜一般罢。有夜风,落叶,赶路人的脚步声,十月的天气里,各路的秀才都要负着行囊,上京赶考去。这样的霜天黎明,他们该要在旅店里醒来,张罗着起身上路罢。他们身着长衫,面如美玉,梳着秀逸的长发,头戴方巾,背着一只书篓,身后跟着一个迷迷瞪瞪的书僮。书僮梳着两个抓髻,混沌未开。他跟着公子读书,为他在旅店扇着风炉煮茶,隔墙的花影摇曳,花语呢喃,他尚不明所以。赶路途中的书僮总是打瞌睡,一边跟在公子后头走路,一边闭着眼睛睡觉。因为醒来了他的话总是很多很多的。进京赶考的霜天路途,有无数的书僮在叽叽喳喳地说话,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前世,我定也曾经走过上京赶考的路途吧?我当然是不好读书的,只好做得一个书僮,性致顽冥,滑稽伶俐,在这样的霜天夜路里,我的嘴巴兴奋地聒噪道:“主人,前方过了兰若寺,就是扫雪圃了。天就该大亮了,昨夜店家传说那里卖世上最好吃的芝麻烧饼。”
沿途的烧饼铺,馒头店,那风霜的路途上,出现在前方的烟火市井,红彤彤的火焰烘烤着大铁锅,开锅时那热雾弥漫的香气,是书僮的志趣所在。
“卖烧饼的是武大郎,还是他家的女娘子呢?”历代的秀才感兴趣的,都是做烧饼的人。一碗阳春面,一盘雪白的鱼羹,一笼雪白俏丽的馒头,都会引发他们的感动,诗兴以及好奇心,非要幻想着什么样巧手的厨娘做出如此动人的食物。他们非要绕到灶门口去看一眼,然而拘束着礼节,只好在墙壁上写下一首诗。这些矫情的家伙,也只有他们,才做出那些文理不通的八股文来。
书僮的背篓里备着笔墨纸砚,随时取用。我们知道书生都是很擅长发感叹以及抒情的,离开家乡进京赶考明明是少年迫不及待的离乡之路,出发之际欢喜雀跃,扬长而去。然而,离乡之路的漫长,令书生一路都在伤怀,看见月亮他们就要油然地思念堂上白发娘亲,夜雨敲窗的长夜让他们辗转难眠,前方的路简直是走不下去了。除了在沿途的餐馆题诗,他们还要在旅馆和驿站的墙壁上,写下很多很多的诗,把自己的心情搞的相当的黯淡。书僮还要殷勤地说出一些劝告和安慰的暖心话,你知道,身为一枚书僮,懂得的道理永远要显得比主人少,所以,书僮总是很务实的,憧憬着前方好吃的馒头,葱油饼,卤猪头这样美好的事物。而路途中,燃烧的火堆里烤一堆红薯,天赐一只荷叶包着的叫花鸡,书僮为此忙得头头是道,愉快无边。虽然他们的主人,那些赶考的书生,对扑鼻的香味视而不见,口无执著,只顾盯着浩渺长空的鸿雁,秋色染红了的第一枝枫叶,忙于寄情言志。最好他们一直这样抬头发呆,不吃不喝,这样就不会发现叫花鸡少了一只鸡大腿。
在那些赶考的光阴里,路途是无边的江山绵延,寒山踏过一重重。沿途有潇潇落叶的红枫林,黄昏投宿的暖老温贫的茅屋,灯火繁丽的集市,沿途皆有酒楼、茶肆、妓院、书馆、驿站,寺庙,道观。而书僮我的人生乐趣,全在于出门远走,霜风里经过陌生的地域,天空中的星星疏淡了,清晨的阳光照耀着陌路之中的寒林溪水,野菊花染香了我年少的脚步。还有一路上遇见的砍柴的老翁,垂钓的渔夫戴着斗笠,乘一叶扁舟,无端端的就做成了一首诗,一阕词。
还有侠客,策马自我们身边驰过,一路轻骑红尘,风将他的斗篷吹起,旗帜一样地在书僮我的视线里久久逗留。我满目艳羡地目送,毫无疑义,他肯定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侠客,从不赶考。侠客是风一样的传奇,而赶考的秀才,是人世间开花的树,花期佳美。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从前的霜天,渡口的芦花,夜色里的客栈,灯笼里的火光,映照在窗纸上的灯光,每一个黎明启程时告别的地方……赶考的路上充满了繁盛的诗歌和邂逅。旅途上,书生们会有诸多场,命中注定的相逢。他们在客栈或寺院的院子里,相互作揖,有点名气的还要道着久仰久仰和不敢当不敢当,如是重复地啰嗦半天。然后他们就一同赶路,一路上相悦地吟诗、作赋,互相对答,作的诗文比随着长路流淌的河水还要绵长和唠叨。他们有的义结金兰,有的相互嫉妒,仿佛前世的怨仇演完一章,今生再接着来。
而那些美好而危险的,花和梦一般迷人而幻灭的事物,花妖,狐仙,杜丽娘,崔莺莺,聂小倩们,她们总是痴情地守候在书生经过的路途中,人世间的伤心断肠事,大抵是经由她们演绎的。邂逅是如此的美好,如梦如幻,而书生总是要上路的,每一场告别都许诺着,待到京试完毕,原路返乡时,定会再重逢。然而,世事无常,某一个斜月西沉,晨光熹微的黎明,执手相看的告别,其实,都是后会无期,不再重逢的永别。
而这一趟上京的漫长旅程,不止是求取功名,更是一场修行。他们要遵守诸多的心法。譬如,沿途不能随意干涉别人家的事情,因为你并不知道背后的恩怨是非。你知道,这些满腹经纶诗书的家伙,仗着识字甚多,他们都是很逞能的。沿途看见孤苦诉冤的无助的人,总好帮忙接济些铜板,写个状纸。写状纸是个很不明智的行为,尤其休书是断断写不得的,哪怕那个求你写休书的婆婆,正在声泪俱下地痛诉着她的儿媳如何凶恶,如何该被当即休掉扫地出门。故事告诉我们,擅长告状的婆婆都是恶婆婆。在祖母讲的“古”里,那些恩怨所化的魂灵,会在秀才们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譬如,一个在旅途中帮人写了一封休妻书的秀才,和一个经过河边为一只渡河无计的小蚂蚁,顺手送一片树叶漂在水上的秀才,所担当的后果,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越往京城,天气渐渐地寒了,途中的风一日一日厉了,京城的城门外,谯搂夜鼓一更一更地敲,呼唤着沿途追随着书生们的那些魂灵:有恩的报恩,有冤的申冤呵!——是风清月白的朝代,光明昭昭,人间一切皆遵循善恶因果报应。
这些去赶考的秀才,若是金榜题名,自然是还要做官的,做官的路途,自然是波谲云诡,浮沉起伏的。最伤心的莫过于一下子重罪在身,或者掉了脑袋。总之,书生们都要渡过波浪诡谲的一生,直到白发苍苍,告老还乡。在我们古早的从前,离开家乡的人们,思乡和还乡,是游子永恒的念想,家园的草木池水都脉脉含情,等你归来。陪伴他进京赶考的书僮,此时大约也是个老苍头了。一身老布衣,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还需要给主人收拾行囊,相伴回乡。还乡之路会让那曾经的书僮,曾经的书生,想起多年前的赶考之路,还有他们邂逅过的那些人。
人的出门远走,大抵是为了白发还乡。这个往复过程便是人生——忙碌,忧心,牵挂,徒劳无益。
当然,还乡之路是静寂的,不再那么风生水起,充满了重峦叠嶂的故事,所有的草木似曾相识,默契无语。这样的归路,像风吹送着落叶,像雪花静静覆盖大地。
别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今夜月光如水,这样柔情的月光简直不像北地的月光。月光掠起我太多的回忆,你知道,一个书僮的记忆也是山长水阔,星河邈远的。
尤其今夜,一阵阵大雁在夜空里飞过,在月光里发出长长的鸣叫声,渐渐远去。它们在月光中的穹宇,驭风飞行,羽翅掠过月亮和彩云,掠过远方黑黝黝的山脉,树林,寂静原野,阡陌人家,从北方往南,往南方飞去。
它们飞过前朝赶考书生的夜行路,也掠过今夜我溯洄不已的残梦。往事与故梦如逝水滔滔,如芦絮飞白,遗留在大地的那前世的脚步仿佛还在赶路,难遣的悲怀令我心酸。
徐沛:共产难民-各有选择(2500字) 1989年6月,邓共把坦克开进北京,血腥镇压以60后为主的八九一代。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中国人遭到共产党的致命打击与残酷摧残,与文革一代和五七一代相比,他们还算幸运,因为不少天安门运动的发起者与参与者都能像当时还是北大研究生的封从德一样躲过邓共的抓捕与囚禁,来到海外,获得自由。 六四屠杀前,经台湾、香港和东南亚来到欧美的华人牧师很难邀请到大陆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六四屠杀让无数大陆人深受创伤,开始参与由教会举办的各种活动,然后相继入教。这些人多半申报“六四血卡”,这之后更多人用脚投票,千方百计来到海外。在异国的外语环境中,华人教会难能可贵,既有助移民适应新的生活,又可以给他们心灵的慰籍。 六四屠杀促使无数大陆人与中共决裂,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我人已在德国,也没加入中共。其时还是研究生的熊焱于1989年6月4日,在北大墙上贴出两张大字报:左边是“丢掉幻想 准备战斗”,右边是“声明 我退出中国共产党。从此与中共断绝一切关系!”1992年,遭受中共囚禁的熊焱流亡美国,加入教会,就读神学院,现为美国陆军少校军牧。像熊焱一样选择信教的八九一代不少,像汤志敏一样在当了基督徒后又走入法轮功的也有。 我没有选择走入西方宗教,虽然我在四川外语学院求学时就乐于与东西方宗教各门各派的信徒来往与交流。因为我从小就信神,热衷探求人生真谛,向往古书比如唐诗中的学仙访道。如果人真能自己选择人生之路,我肯定不会获得学位后继续留在德国。可惜只要中共不垮,我就有国难归,因为我已习惯自由,不可能放弃人权,接受在中共领导下的特权。这也算人命天定由不得我。我庆幸自己能在36岁前读到《转法轮》,从中找到在东西方宗教经典中都没有找到的人生答案。我也更知道珍惜身在德国的自由,也更有精力声援海内外的反共志士。 封从德在采访中透露,天安门一代在六四屠杀后,大约三分之二出国。大多数上学后工作,有的经商,其中“小部分人完全放弃理想,甚至与中共合作”;有的换了轨道,但还没有放弃理想,比如熊焱;封从德认为自己处于“脱轨状态”,因为“一直忘不了六四“。他原来是北大遥感所的硕士生,因为逃亡途中的神奇经历,到法国后进入索邦大学研究宗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医的宇宙论与道教的关系》,他也获得法国工业部的工程师文凭。他九八年起就转到电脑行业,自建六四档案网64memo.com。 身在海外的华人既有信仰自由,又有言论自由,可惜好些人不知道珍惜甚至滥用大陆同胞没有的自由。他们也把群发件投入我的邮箱,有时会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我因此获知封从德对基督教信仰与美国现代文明的看法,其中下列论述甚合我意,特此分享: 有人宣称真理是唯一的,听起来不错。 只是,人是罪人(基督教圣经中的“罪”,其实古希腊文是“过”、“不中”,即“不中靶心”的意思,这样说来,人人有“罪”也就很好理解了),因此,人人有局限。因为有局限,所以不可能认识真理的全貌,各人所知的“真理”,必然如盲人摸象。大象还是大象,但每个盲人/罪人的认识就不一定相同,若各执己见,就很难沟通了。由此可见,宣扬“真理是唯一的”,这可以说得过去;但如果加上一句,说“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就是我(们)认识的那样”,那就麻烦了,一切宗教战争都是以此为借口的。 而认识真理的过程,则好比登山,有境界的高低。通往山顶的路不止一条,只有临近山顶,才能明白,其它很多条也都能通向山顶。 有些人顺一条路被带到半山腰,领路者自然要宣称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跟随者也自然需要这样的信心,才能坚定不移地向上攀登。这就是大多数信徒的状态,尤其是新信徒刚刚向上攀登时的状态。这时的“唯一性”与排他性,既很自然,也很必要,因此很容易以己之雅比人之俗,这样才能巩固信心。但也是因为境界不够高,眼界不够宽,而形成严重的促狭与偏见,不知道也不愿意相信其它路也能登顶。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种现象,叫“新教徒综合症”,他们极其热忱,急不可耐地要把自己刚刚认识到的真理传遍全世界,同时也有极强的排他性甚至攻击性。他们不是说“这是辣子鸡丁,很好吃,你也试试?”,而是说“这是辣子鸡丁,最好吃,你一定要吃”,有时候还会加一句,“不吃就下地狱”。 ……无神论在认知方法上是荒谬的。无神论是另一种信仰,一种比有神论更为坚固、但违背基本逻辑方法的信仰。当然,大多数自称无神论的人,其实是不可知论或怀疑论者,他们还是相信有一个“本体”存在的。 那么,我们在山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很多古人比较有福气,那时他们没有太多选择,其它道路根本没听说过,于是就一路上升,直到山顶。当然,也有很多被盲目地带到了山洞中或小山顶而走不出来。 问题是,现代人在资讯极度发达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先用广度与深度结合、再一门深入的办法比较合适:先对各教都稍微了解一下,进去试一试,然后选择对自己合适的道路奋力向上。这时就需要“正心诚意”……“邪心修正法,正法亦邪”。所以正心很重要,假如真的一开始走上了邪道,正心(也就是上帝在我们内心的良知声音)也会带我们改邪归正。 以上是封从德的观点。在我看来王若望等昔日共产党员就是青少年时被鲁迅们误导上了邪道,好在他们的良知没有泯灭,还能在六四屠杀后幡然醒悟,从此与共产党决裂,走上正道。同样,有的基督徒根本算不上真信徒,因为他们违背耶稣的教诲。比如敢于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对他们不了解的人事加以“毁谤”。违背圣经,既“毁谤”又“随伙毁谤”的基督徒即使不是共特,也不能算基督徒。 我因六四屠杀开始反共,因获知法轮功开始上网,我发现法轮功学员中也有共特。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修身养性的佛家大法,如果谁既不真诚又不善良,那么,他连正派人都算不上,遑论法轮功学员。至于我算不算法轮功学员,欢迎读者自己判断。总之,我乐于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与观点,本着善心评判进入视线的是非,供读者参考,为历史见证。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