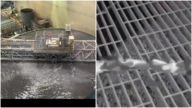一些省份的高死亡率,证明了饥荒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这一事实。由毛派激进分子领导的这些省份,前些年实际上是粮食净出口方,如四川、河南和安徽。位于中国中北部的河南省受影响最为严重。1960年,死亡率从约15%的正常水平飙升至68%,而出生率则从之前30%的平均水平降至11%。结果,一年内人口减少了约200万人(占总数的6%)。与毛本人一样,河南的党内积极分子也确信,一切困难都是由农民隐藏私人存粮而引起的。信阳地区(1,000万居民)此前建立了中国首个人民公社。据该地区的书记说,“问题不在于缺乏食物。有足够数量的粮食,但90%的居民正遭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困境。”1959年秋,阶级战争暂时被遗忘,对农民发起了一场军事式攻势,使用的手段非常类似于抗日游击队组织所使用的。至少一万名农民被监禁,许多人在狱中被饿死。下令砸碎所有尚未变成钢铁的私有餐具,以防止人们通过偷窃公社的食品供应来养活自己。甚至还禁止生火,尽管冬天来临。镇压的暴行令人恐惧。成千上万的在押者遭到系统性的折磨;儿童被杀,甚至被煮沸并用作肥料──这正处在发起一场全国性运动叫人们“学习河南方式”之际。在安徽,指定的意图是,即使99%的人口死亡,也要保持红旗飘飘,干部又回到了活人祭祀和用烧红的烙铁折磨人的传统习惯,其数量之多更是吓坏了幸存者。葬礼被禁止,以免变成抗议游行。接纳众多被遗弃的儿童住宿也被禁止,理由是“我们接纳得越多,被遗弃的也就越多”。试图强行进入城镇的绝望村民遭机枪扫射。凤阳地区逾800人就这样死去。12%的农村人口,即28,000人,以某种方式受到惩罚。在一场对农民的真正战争中,这场运动占了很大比重。用让-吕克.多梅内克(Jean-Luc Domenach)的话来说,“乌托邦侵入政治与社会中警察恐怖的侵入在时间点上非常契合。”某些村庄饿死人数达到50%,在某些情况下,唯一的幸存者是滥用职权的干部。在河南和其它地方,有许多同类相食的案例(官方记录了63例):儿童有时根据一项公共决定被吃掉。
1968年,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被当局追捕的18岁的红卫兵魏京生,与家人一起在安徽一个村庄里避难。在那里,他听到了很多关于大跃进的内情:
我一到这里,就经常听到农民们谈论大跃进,好像这是他们曾奇迹般逃脱的某种大灾难。我对这个话题颇感兴趣,就对他们进行了详细询问,结果我很快也确信,“3年自然灾害”并没有那么自然,相反,是一系列政治大错的结果。例如,农民们说,在1959年至1960年“共产风”(大跃进的官方名称之一)期间,他们饿到在水稻作物等待收割时甚至没有足够力气来收割,否则对他们来说这会是较好的一年。他们中许多人死于饥饿,眼睁睁看着稻米落到田里,被风刮走。在那里一些村庄,实际上没有剩下可以进行收割的人。一次,我和一位亲戚碰到一起。他住在离我们村庄不远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被遗弃的村庄。所有房屋都失去了屋顶。只剩下泥墙。
想到这是一个在大跃进期间(当时所有村庄都被重组和搬迁)被遗弃的村庄,我就问为什么没有推倒那些墙,为更多田地腾出空间。我的亲戚回答说:“但这些房子都属于民众,不经他们允许,就不能把它们推倒。”我盯着那些墙,无法相信那里实际上有人居住。“当然有人居住了!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共产风’中死了,再也没人回来过。然后,土地在邻村之间进行分配。但因为看起来其中有些人可能会回来,生活区从未分配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人回来。”
我们一起走在村旁。阳光照在从土墙之间冒出的翠绿的杂草上,突出了与周围稻田的反差,让景象更显荒凉。在我眼前,在杂草丛中,出现了我曾被告知的一幕──一次宴会。在这些宴会上,家庭之间交换孩子,目的是吃掉他们。当那些家庭咀嚼别人的孩子的肉时,我可以看到他们担忧的面孔。那些在附近田地里追逐蝴蝶的孩子,似乎是被父母吞食的孩子转世。我为孩子们感到难过,但并不像我为其父母那样感到难过。是什么让他们在其他父母的眼泪和悲痛中吞下那个人肉──他们即使在最糟糕的噩梦中,也绝不会想像品尝的人肉?那一刻,我明白了,他──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屠夫,“像他这样的人,人类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几千年来都未曾见过”。毛泽东及其党羽,与他们犯罪的政治制度一起,用饥饿把父母们逼疯,并促使他们将自己的孩子交予他人,且接受他人的肉以缓解自己的饥饿。为了洗刷掉他在暗杀民主(暗指百花齐放陷阱)时所犯的罪行,毛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迫使千千万万饿得晕眩的农民,彼此用锄头杀死对方,并因儿时同伴的血肉而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并非真正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毛泽东及其同伙。最后,我明白了彭德怀从哪里找到了力量来抨击毛领导的党的中央委员会;最后,我明白了农民为何如此厌恶共产主义,以及他们为何从不允许任何人攻击刘少奇的政策──“三项自由和一项保证”。这只是出于充分和简单的原因,即他们绝不愿让吃掉自己血肉的惨剧再次上演,或者在本能疯狂的时刻杀死其同伴吃掉他们。这个理由比任何意识形态考量都重要得多。
在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刻,一个拥有超过3万英里铁路线和广泛的无线电及电话网络的国家,正遭受一场生存危机的蹂躏。那样的危机曾困扰现代化之前的欧洲。如果在18世纪,这场危机的规模会影响全世界的人口。确实有无数人尝试煮草和树皮做汤,从城镇的树上剥掉树叶,徘徊在乡村道路上,极度渴望找到任何可以吃的,徒劳地尝试袭击食品车队,有时拚命地结成帮派(正如在河南的信阳和兰考地区一样)。没有发送给他们任何吃的,但有时有理应为饥荒负责的地方干部被枪决。为了搜寻藏在地下的玉米,当局对全国各地的房屋进行了武装袭击。疾病和传染病的大量增加,进一步提升了死亡率,而出生率几乎降为零,因为妇女因营养不良而无法怀孕。劳改营的囚犯并不是最后一批死于饥饿的人,尽管他们的境况与前来营地讨吃的的附近农民同样危险。1960年8月,在经历了一年的饥荒之后,包若望的工作队有四分之三的人死亡或垂死,幸存者沦落到在马粪中搜寻未经消化的麦粒、吃牛粪堆里发现的蠕虫。营地里的人在饥饿实验中被用作豚鼠。有一次,为了研究对消化的影响,将面粉与30%的纸浆混合,做成了面包。而在另一项研究中,把沼泽浮游生物与米汤混合在了一起。第一项实验在整个营地引发恶劣的便秘,导致许多人死亡。第二项也导致了诸多疾病,很多本已变弱的人最终死去。
就整个国家而言,死亡率从1957年的11%上升到1959年和1961年的15%,1960年达到29%的顶峰。出生率从1957年的33%下降到1961年的18%。不包括出生赤字(可能多达3300万,尽管一些出生只是被推迟),与1959至1961年饥荒有关的生命损失约在2000万至4300万之间。该范围的下限是自1988年以来中国政府所使用的官方数字。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很有可能是最严重的饥荒。第二大饥荒于1877至1878年发生在中国北方,夺走了900万至1300万人的生命。1932至1934年在类似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袭击苏联的那场饥荒,造成约600万人丧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于大跃进期间的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农村的死亡率比城市的高30%至60%。1960年,它翻了一番,从14%上升至29%。农民们设法通过消费自己的家畜,来略微延缓饥荒的影响,而消费家畜相当于耗尽了他们的生产资本。1957年至1961年,48%的猪和30%的乳畜被屠宰。1959至1962年,让给棉花(当时是该国的主要产业)等非食品作物的表层土地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这种产量的下降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制造业。尽管1959年以后农民市场重新开放以刺激生产,但要价很高,且可得的数量很低,以至于很少有饥民能找到足够的食物来生存。例如,1961年,市场上的猪肉价格比国营商店高出14倍。在以畜牧为主的西北部,粮食严重缺乏,而粮价涨幅超过了饲料价格。在甘肃,1962年人们仍死于饥饿,口粮仅相当于“半饥饿”状态官方限额的一半。
对于数百万条生命为建设共产主义而被迫牺牲,无论是因为未意识到,还是更可能因为漠不关心,国家是以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罪恶的措施来回应(如果这样的词可以用在这里的话)危机。主要对苏联的粮食净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加至1959年的420万吨,1960年仅下降到1958年的水平。1961年,实际进口了580万吨,远高于1960年的66,000吨,但这依然太少,无法养活饥民。出于政治原因,美国的援助遭到拒绝。世界其它地方本可以轻易帮助应对这场大灾难,但一直不知道它的规模。在自由市场上一公斤大米价值2至4元人民币的时候,每年对农村穷人的援助总计还不到4.5亿元,即每人0.8元。中国共产主义吹嘘其可以移动大山、征服自然,却丢下这些信徒让其死去。
从1959年8月到1961年,党表现得好像无力给予帮助,只是袖手旁观事件的发展。批评毛全力支持的大跃进,是件危险的事。但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该政权二号领导人刘少奇最终迫使主席采取守势,并强制部分回归较容易的集体化形式。集体化曾是人民公社发明前的政策。再次允许人们拥有少量土地,重新开放农民市场,开设小型私人作坊,把劳动组再分为劳动队──相当于早先村队(village teams)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该国迅速摆脱了饥荒,但并没有那么快摆脱贫困。1952年至1958年间稳步增长的农业生产已经迷失了方向,其影响持续了20年。只有在“填饱肚子”(如毛所说会发生在人民公社)时,信心才会回归。1952年至1978年间,农业总产量翻了一番,但在此期间,人口从5.74亿增至9.59亿,人均增产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在大多数地方,至少到1965年(河南晚至1968~1969年),产量才达到1957年的水平。总体而言,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大跃进对资源的惊人浪费导致它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直到1983年,生产力才再次达到1952年的水平。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目击者报告一致认为,中国仍是一个极度贫困的传统乡村社会,充当一个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体,奢侈品极为罕见(例如,食用油就像金粉一样金贵)。大跃进使人们极度怀疑该政权的宣传。农民对邓小平经济改革反响最为热烈,且是人民公社启动20年后重新引入市场经济的推动力,这不足为奇。
1959年至1961年的各灾难是该政权的一大秘密,许多外国访客也设法否认。它们从来没有因其真实情况而获得承认。1962年1月,刘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称,饥荒70%都是由人为错误造成的。当时,这一看法并未得到众人赞同。不直接归罪于毛泽东,就不可能说出任何更进一步的话。甚至在他死后,在1981年电视播放的中共对他一生的最终裁决中,也没有批评大跃进。(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