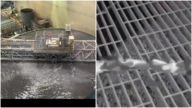葡萄牙自15世纪以来就在非洲海岸保持存在,但在把一个庞大帝国(其自身大小的25倍)变为殖民地方面却成为新来者。1884至1985年欧洲大国在柏林会议上瓜分非洲时,葡萄牙才被授予殖民权。这种迟来而肤浅的殖民化阻止了殖民地各民族间产生一种整体感。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起武装斗争的团体被迫依靠反殖民情绪。这种情绪比任何假定的民族主义抱负都强大得多。这些民族主义团体意识到自己极端主义观点的障碍,因此在独立后就把重点放在了inimigo interno(“内部敌人”[enemy within])身上。这指的是传统的酋长、曾与殖民者相勾结的人以及政治异见者。他们所有人都被控危害国家。这就是斯大林与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之间撕裂的政治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几乎没有建立代议制民主的动机,尽管葡萄牙殖民主义政权很快就倒台了。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面对白人殖民地人民的狂怒,1974年在里斯本上台的军官宣布支持这些殖民地的独立。就在此时,葡萄牙军队仍然牢牢掌握着安哥拉。1974年7月以后军队的迅速撤离为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开辟了道路。该政府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争取独立的3个组织所组成: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Nacional de Libertação de Angola;FNLA)以及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UNITA)。1975年1月15日,独立条约在阿尔沃(Alvor)签署时,新的葡萄牙共和国承认这些组织为“安哥拉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时间表看起来颇有前景:将于9个月内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并于1975年11月11日宣告完全独立。但在40万名葡萄牙人于1975年2月至6月离开以及3个组织间出现紧张关系之后,联合政府(MPLA在其中负责掌管信息部、司法部和财政部)很快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血腥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6月14日的纳库鲁(Nakuru)停火只是被各方用作休战,目的是加强储备并为其外国盟友的干预做准备。
从1974年10月起,苏联大大增加了对MPLA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该组织也得到了葡萄牙军队左翼即所谓的武装部队运动(Armed Forces Movement)的支持以及“红色海军上将”安东尼奥.罗莎.科蒂尼奥(António Rosa Coutinho)的支持。他常驻在罗安达(Luanda),已被葡萄牙政府委以监督安哥拉向独立过渡的责任。1975年3月,首批古巴和苏联顾问抵达该国。菲德尔.卡斯特罗后来用以下措辞描述了这一决定:“非洲现今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正是在那里,存在着从部落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大希望,这种过渡不会经过世界其它地区所被迫经历的各个阶段。”联合政府于1975年8月14日垮台后,“英雄越南”(Vietnam Heroico)号船停靠在罗安达,船上有数百名(大多数是黑人)古巴士兵。到10月23日南非站在UNITA一边进行干预时,苏联和古巴顾问已达7,000名。MPLA及其资助者并没有很认真地看待UNITA;《真理报》将其描述为“一支充斥着中国和中央情报局雇佣兵并得到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援助的滑稽军队”。这一描述有些道理。UNITA最初是个毛派组织,一直在与魔鬼签约。其混杂的组织和盟友反映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道路的苦涩现实。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坐在和皮克.波塔(Pik Botha)所坐的同一张桌子旁,这一事实应该不会让那些记得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定的人感到惊讶。
苏联和古巴的空中支援证明对该政权的生存起了决定性作用。1975年11月11日, MPLA和UNITA分别宣布该国独立。与此同时,这颗葡萄牙殖民地中曾经的明珠的地图被重新绘制出来。MPLA占据着海岸线,不仅包括港口,还包括石油储备和钻石,而其对手们(其中UNITA很快成为最重要的对手)则占据着北部地区和中部平原。
在南非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干预之后,西方列强和南部非洲其他领导人更容易厘清不同的团体。对于莫桑比克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来说,从各种力量的组合中,可明显看出斗争的残酷性:“在安哥拉,两方正在相互对抗:拥有盟友和傀儡的帝国主义以及支持MPLA的进步势力。就这么简单。”MPLA无可争议的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是一位被同化的黑人,出身于新教牧师世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亲苏联的葡萄牙共产党的成员。MPLA创立于1956年。它的许多干部,比如胡利奥.马特乌斯.保罗(J. Mateus Paulo)和阿丰索.多明戈斯.范杜嫩(A. Domingos Van-Dúnem)都曾于60年代在苏联接受过培训,并精通盛行的马列主义理论。除了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这种培训外,其中一些人,例如J.纳姆巴.耶米那(J. Njamba Yemina),在国外时也曾接受过军事训练,要么是在苏联,要么是在古巴的游击队学校。
掌权后,MPLA在罗安达的代表大会(1977年12月4日至11日)上决定,是时候从人民阵线类型的运动转变为按照布尔什维克路线组织的先锋党了。MPLA领导人意识到,只有这样的政党才会被允许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席这次大会的劳尔.卡斯特罗立即承认新的MPLA劳动党为“能够正确表达劳动人民的、唯一可能的手段”。
政权的理念(idea of the state)作为“唯一能够实施一党决定的工具”,意味着要对对手党派保持极度警惕。这些党派可能正在掩盖它们在左翼措辞背后的反革命本质。不足为奇的是,在那之前一直是北半球共产党政权专利的许多“反路线偏差的”做法,开始在安哥拉出现。甚至在布尔什维主义被正式设为安哥拉新的信仰之前,内图就已经在该领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1975年2月(在葡萄牙军队的帮助下),他袭击了由奥文本杜族(Ovimbundu)干部丹尼尔.捷宾达(Daniel Chipenda)所领导的“东部起义”派系。当时, 捷宾达声称,这只是自1967年以来对MPLA异见者一系列整肃中的最新一段插曲。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1974年2月发布的MPLA公报。该公报声称,“发现并摧毁了”一起旨在“对总统及其几名干部进行肉体消灭”的内部反革命阴谋。
内政部长、内图的主要对手之一尼托.阿尔维斯(Nito Alves)在1974年4月25日的系列事件中曾出现在罗安达。这些事件敲响了殖民政权的丧钟。在没有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他设法赢得了相当大比例的城市黑人的支持,方式是通过拒绝给予白人安哥拉国籍,除非他们能表现出明显的反殖民主义行为。阿尔维斯受到了居委会网络的支持,这要归功于他所说的“大众权力”(poder popular)。这是他毫不犹豫地使用很明显是斯大林主义的做法而获得的。这些做法对于受害者来说并不意外,因为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毛主义传统下长大的。由于相信从苏联、古巴人和葡萄牙共产党人那里获得的支持承诺,阿尔维斯于1977年5月27日尝试发动政变,以阻止一场刚刚开始的对其党羽的清洗。当行动失败(部分是由于阿尔维斯外国顾问的犹豫)这一点变得明朗化时,内图在电台广播中说:“我确信,民众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被迫有些严厉地对待参与这些事件的人。”密谋者被指控为“种族主义、部落主义和区域主义”,遭到彻底的清洗。中央委员会和国家主要机关的成员被完全更换,首都发生流血冲突,镇压深入到各省。在恩贡扎(Ngunza)(南宽扎[South Kuanza]),204名路线偏差分子于8月6~7日的夜间被杀;该数字为1991年以后幸存者拿出的数字提供了可信度。他们报告说,在那个时候,数千名MPLA成员被彻底清除。MPLA中央委员会成员阿尼巴尔.萨皮利尼亚(Anibal Sapilinia)在卢埃纳(墨西哥)清算了武装部队中的许多政治委员。
在这次未遂政变之前,尼托.阿尔维斯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在报纸《罗安达日报》(Diario de Luanda)上的专栏以及在两个广播节目“Kudibanguela”和“Povo em armas”中的评论。这两个节目不断地谴责该国恶劣的生活条件。这些节目证实了某些地区确实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他的支持者甚至谈到饥荒)。他们还强调了被迫为该政权工作的城市受薪工人的精疲力竭。1975年11月推行的一项法律和1976年3月的一项法令,通过对“工会外”(extra-union)(即反党)罢工进行入罪化,并营造充斥着“生产和抵抗”(Produce and resist)等口号的政治气氛,来加强制造业的纪律。开始出现新的抗议形式。它超越了对战争的一贯谴责和白人统治后的混乱状态。安哥拉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繁荣发展,但在1975年崩溃,尽管国家对经济体系进行了控制,但政府却发现,越来越难以否认经济正在逐渐被美元化。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对普通民众生活条件漠不关心的统治阶级开始出现,部分是由于MPLA对权力的垄断,部分是由于难以获取外汇。外汇在黑市上转手的价格是其官方价格的50倍。十多年来,对于该国内部情况到底是怎样的,甚至不可能有一个不错的认识。政府成功地将由石油出口支持的城市市场与本地生产商分离开来。国家或多或少地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农村撒手不管。冲突双方在农村地区实行强制征兵。“饥荒”一词在官场上被谨慎地避免使用,但1985年被世界粮食组织用于一则警告中。随着苏联改革(Perestroika)的出现,安哥拉政府开始公开承认情况的严重性,导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于1987年初宣布,前一年安哥拉有数万儿童死于饥荒。
尽管有卡宾达(Cabinda)产油区创造的财富,但国家的行政和军事资源相当有限,该政权几乎未做什么尝试来进行集体化和农村重组。尽管如此,农村地区对政府仍颇为怨恨。税收征管方面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贸易壁垒以及城市市场的消失,意味着农村常常不得不自谋生路。独立13年后,安哥拉当局发表了一份正式报告。该报告是基于农学家勒内.杜蒙(René Dumont)的调查结果。他尖锐批评安哥拉的贸易条件,因为它们没有承认农民所作贡献的真实价值。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对沿海地区日益上升的敌意。在那里,克里奥尔人或混血同化民(assimilados)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其中许多人在MPLA担任职务。
正是在农村人口(其中许多人也讨厌外国人)中,若纳斯.萨文比的UNITA党在其起源地奥文本杜人的地区以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尽管萨文比对民众提出的要求与政府一样,UNITA的支持度却有所增加。随后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农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的战争,而不是一场由MPLA领导的针对农民的斯大林式战争。UNITA受到里根政府的支持,但从毛主义中汲取了自己大部分思想,因此其领导人总是急于渲染城乡间的冲突;他们经常以“非洲人民”的名义谴责MPLA的克里奥尔贵族。尽管如此,仍难以衡量在剧变席卷苏联阵营之前农民对萨文比事业的支持程度。1988年12月22日和平协定在纽约签署后,南非人和古巴人最终撤军之际,MPLA向西方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预期的结果。1990年7月,MPLA领导层承认了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必要性。这一变化被证明是UNITA失败的原因。它在1992年的选举中遭遇了惨败。
MPLA在独立15年间所经历的不可否认的变化,实质上是民众普遍抵制MPLA的党国理念之结果,也是15年经济不稳、强制征兵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惨痛经历之结果。
朝着多党制民主发展的过渡期,显然不是开始搜寻负责秘密警察或对人权侵犯负责的人的时候。像在苏联一样,许多责任人都是少数族裔成员,从未被迫对其以前的活动负责,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内部存在基本的连续性。除了清洗中幸存下来的几小群人外,没有哪个主要政党曾经要求对数以万计受害者的失踪进行调查,正如大赦国际措辞严谨的报告所说的,他们的命运并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公平标准”。(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