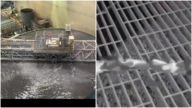文革中,北大东语系主任、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季羡林语)
在《牛棚杂忆》里,季羡林专门回忆了这段经历。
他说,东语系批斗开始后,原来只让他做配角,很快又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激烈的敲门声响过之后,进来了两个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押解着他到了外文楼。进门先在楼道里面壁而立。他仍然是什么都不敢看。耳旁只听得人声嘈杂。他身旁站着两个面壁的人。他明白,这是陪斗者。过了一会,只听得屋里一声大喊:“把季羡林押上来!”从门口到讲台也不过十几步。然而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呀!四只手扭住了他的胳臂,反转到背上,还有几只手卡住脖子。他身上起码有七八只手,距离千手千眼佛虽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经够可观的了。可是在这些手的缝里还不知伸进了多少手,要打他的什么地方。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他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他戴遍了。他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我心里一愣,几乎吓昏了过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的仇恨,都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这个挂头牌的主角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地上没有缝,我是钻不进去的。我就‘安之’吧。”季羡林回忆道。
“打倒”的口号喊过以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接下来发言的人,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他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他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捏造、罗织、说谎。发言者说到激昂处,“打倒”之声震动屋瓦。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他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不久有人把他从地上拖了起来,接着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打人者中有两人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季羡林说,“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动地表?)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这时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回头一看,后头没了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腔子里,喘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黏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这样走回了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