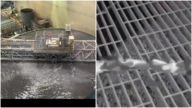1966年9月3日上午,傅雷家的女佣周菊娣按时起床准备为他打扫卧房的时候,发现一向早起的傅雷夫妇直到九点多钟还没有任何动静,她预感不妙。
上海市长宁区派出所户籍警察左安民不久赶到,当他把卧室落地钢窗上的傅雷和妻子朱梅馥从自缢的绳套上解下时,二人的生命已经静止了。
这一年,傅雷五十八岁,朱梅馥五十三岁。
傅雷,著名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宣告为右派分子。
之前傅雷就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雷却再也不能幸免。 当天夜里,傅雷夫妇在家里沉默地坐着,许久他才开口,然后欲言又止:“如果不是阿敏(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傅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砸开了傅家的大门。其实傅雷本与音乐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音乐学院会来抄家,是因为当时的钢琴系主任李翠珍是傅雷的妻子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当初从香港回来时给傅雷写过信征求意见。此时李翠珍已被打成特务,这封信自然成了傅雷是潜伏特务的罪证,顺着这条线索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当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傅雷。
随后,红卫兵不但抄了傅雷的家,还对他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批斗罚跪。傅雷家的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尽管他们之前对灾难已有所预料——8月23日的时候,傅雷就对妻子说过:“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就让他们来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但当风暴真正袭来时,政治的铁拳还是将仅存的那一点尊严击得粉碎。
于是,傅雷开始为自己的死亡准备一切:8月27日,与朋友告别,宣布自己会带着夫人一起走。朱梅馥也曾对傅雷说过:“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 那时她死心已定、去意已决。面对满地的狼藉,她对保姆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1966年9月2日,大约在晚上八点的样子,夫妇俩吃晚饭,朱对周说:“明天小菜少买点。”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在写好遗书之后,傅雷夫妇怕凳子碰倒后发出声响,先在地上铺好棉被,然后将床单撕条打结,随即自杀。
两个知识分子,优雅温文,却被红卫兵们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