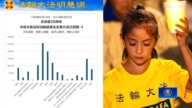(接上文)
水牢
二零零四年,联合国关于法轮功遭受人权迫害的报告中提到:肖先生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被关在北京怀柔看守所的“水牢”中。他被剥去衣服赤裸的关在一只里边带钉子的小铁笼子里。在一个暗室里,笼子被侵入污水中,污水淹到他的胸口或脖子。他被关在笼子里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尿和粪只能排泄入水中。
水牢作为一种行刑的牢房为很多人所熟悉,没想到今天仍然存在着。我们一直以为,中共酷刑的惨烈程度超过古今中外的所有酷刑,即使没有水牢,中共在摧残法轮功学员时,也能让他们承受超过坐水牢许多倍的痛苦。法轮功学员在承受冻刑这类酷刑时,有些不是比传说中的水牢更残酷吗?
屎牢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在山东省沂水县沂水镇城郊洗脑班,沂水镇综治办主任李红伟与副主任王建军,用便桶盛了屎和尿,搅拌成屎汤。泼在法轮功学员睡觉吃饭的屋里,强迫法轮功学员陈允明把没泼到的地方拿笤帚扫均匀。有的人头上、身上都被溅上了屎渣。臭气满屋难闻,然后恶徒们再不断的往屋里泼水,整个屋子变成了屎牢。以后又连续几天,邪恶们每晚用凉水泼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上。法轮功学员在寒冷中度过漫长的黑夜。
这种屎牢只有中共恶徒才做得出来,因为要想制造这种屎牢,发明者的心灵得十分的龌龊和无耻,而这些肮脏的因素,只有中共党徒才完全具备。
雪地上的冷冻和侮辱
河北三河市新集镇的不法官员迫害法轮功学员肆无忌惮。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镇政法委书记杨少林、武装部部长皮万成,绑架了几个法轮功学员到镇派出所,并给戴上手铐,铐在院子里的水泥柱上。派出所所长王振东强迫法轮功学员潘振芳和孟召民脱光衣服、鞋和袜子,只剩一条三角裤衩,光身赤脚,踩在有雪的地上背铐着。孟召民被铐在院子里的水泥柱上,潘振芳被铐在大门外的广告牌上,招来了好多老百姓围观。好多好心人向他们为法轮功学员讲情,说时间太长了,天又这么冷,别把人冻坏了。可这些不法之徒却一点都不动心,一点人性都不讲,根本听不进劝告。一直到天快黑了才给打开手铐,放开两位大法弟子的时候,全都浑身青紫、没有知觉,胳膊抬不起来,脚不会走路了,一动就摔跟头。
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开始,大队长杨泽民等警察对崔秀珍老人进行强制“转化”。崔秀珍老人被警察拖到雪地里,强迫她趴在雪堆上、坐在冰上。还弄来大便强迫她趴下去闻,臭味儿小了,再泼上开水。有时折磨到凌晨两点,才拖架回监室。
冰天雪地里的暴行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六点,恶警逼迫董亚珍等法轮功学员到外面挨冻。因为外面太冷了,大家拒绝出去。一个叫秋艳的恶警指使犯人把董亚珍等法轮功学员硬拉出去。外面的风很大,大家的身体冻的发抖。而旁边的恶警都戴着口罩,穿着两件棉大衣,两个小时一换班。
黑龙江省依兰县三道岗镇中学教师左仙凤,于二零一零年六月下旬被绑架到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遭到残酷的迫害。她的母亲这样控诉前进劳教所的罪恶:“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外面下雪了,零下二十多度。前进劳教所不许我们家属送棉鞋、棉衣,我女儿只好穿着单薄的衣服。而大队长王敏硬找茬逼我女儿穿着薄衣、单鞋出去扫雪。遭我女儿拒绝后,王敏就指使女警和犯人逼左仙凤到雪堆里罚站一小时。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左仙凤被整整冻了一个多小时,差点被活活冻死,她们才将我女儿放回到室内,但又接着罚我女儿站一宿,之后又马上给她上大挂吊起来,一边骂、一边用电棍电。”
原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六中声乐教师任淑贤,九九年十一月被劫持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三九天在室外冷水洗漱,手指冻僵,像白蜡一般,常有人冻的哇哇大哭。有一次因任淑贤超过洗漱时间,被管教祝铁红在室外罚站半个多小时,刚洗完的头发立刻冻成一团冰,棉袄领因湿冻硬,脖子冻僵,耳朵冻的失去知觉。
黑龙江冬天的外边有多冷?警察需要穿两件棉大衣;法轮功学员刚洗过的头发被冻成了一团冰;是谁在这个时候逼法轮功学员穿着单衣单鞋去扫雪?然而,法轮功学员在冰天雪地遭到的摧残又何止是这些?
山东蒙阴县坦埠镇南极山村农妇赵秀芳,二零零零年底进京上访被绑架,遭疯狂毒打后,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北京怀柔县看守所。她看见一位女学员来了例假,被弄到牢外,站在雪地里,头上几次被泼上凉水,头上、身上全成了冰块。
现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大石庙曲轴厂家属楼的韩立萍,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十,同几个法轮功学员到北京打横幅,遭到绑架。她自述说:“下午五点多钟,我和其他五个同修被劫持到北京六里桥派出所……那年雪下的特别大,六里桥的恶警不让我们穿鞋,光脚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一天。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了,把一个叫张秀兰的学员叫去,等她回来时已经十二点多了,看到她半边脸是青紫的,胳膊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全身都冻成冰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恶警把她的鞋扒下,衣服扒下,就穿着背心,让她光脚站在雪堆里,用电棍电她,电死过去就浇凉水,醒来后再电再浇,一直到两根最大的电棍都电没电了才住手。
“第二天上午八点,恶警把我和另一同修带到院里,把我们的鞋扒下,光脚站在雪堆里,把棉衣脱掉,穿着背心,把我们双手铐在铁柱子上,还往我们的背心里放雪团,从上午八点一直到下午三点。这些恶警穿着棉大衣,厚厚的大皮鞋,就在院子里放鞭炮,不一会他们冻的都像缩头乌龟一样缩回屋里去了。可我们穿着背心,光着脚在雪堆里站了七个多小时,回屋后让同修在电风扇下吹了两个多小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韩立萍她俩在雪堆里站了七个多小时,为什么回屋后还让法轮功学员用电风扇吹她们呢?因为她们冻得太严重,身体得慢慢的恢复,不然的话,极易造成残疾。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迫害的残酷。
河北省平泉县法轮功学员刘文季,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抓,在北京顺义派出所遭到毒打,五、六个恶人围着打。在那样严寒的天气里,让他赤身裸体到深夜十一点左右,之后往身上浇凉水,水流地上结成冰,强迫他坐在冰上,大约冻了四、五次,累计七个多小时,身体部分部位失去知觉,一直折磨到凌晨二点多钟。
二零零一年初,去北京上访的重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北京房山地区看守所。法轮功学员们双手被捆,吊在大树上,恶警往树的根部浇水,形成圆圆的冰包,学员们双脚踏在冰上。京城的冬夜格外寒冷,到处是一尺以上的冰锥,冷风吹来,雪花飞舞,人浑身颤抖,牙床不停地磕着。法轮功学员没有妥协,“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在看守所的上空回荡。
山东省招远市宋家镇丛家人村的法轮功学员丛成芬,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道,于二零零零年春节前到北京上访,后被绑架回宋家派出所。她自述道:“时值隆冬腊月,寒风刺骨,冰天雪地,镇长杨少亮、副镇长郭长春、恶人苑东玉一伙恶徒七八个人不仅对我们拳脚相加,辱骂,还逼迫我们坐在结了冰的地上,不准起来,还要把腿伸直,稍一动就又被恶人拳打脚踢。地上的冰坐化了,再被拖一个地方继续坐。我们每个人的衣服从腰以下全部湿透了。有的学员的裤子都被冻在了冰地上,手脚麻木,全身僵硬,这样连续四五个小时之久。我还被他们将鞋子脱下,逼我光着脚站在雪地上一个多小时,脚都冻得麻木了,失去了知觉。”
二零零一年九月底,广东省汕头市中级法院刑二庭书记员谢纯锋,再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被绑架到北京大兴区看守所。在此期间,国保恶警为得到他的真实姓名, 经常对他拳打脚踢。并于二零零一年农历十二月,由北京市大兴区国保姓周的主任和姓任的探长,将他绑架到大兴区郊外某农场里的洗脑班进行折磨,逼问真实姓名。曾在冬天最冷的黑夜十二点,北京国保恶警把谢纯锋剥光衣服,仅存裤衩,赤身裸脚,强行拖到雪地上,一次次打倒在雪地上逼问姓名,并拖到冰封的池塘的冰上,冻了他半个多钟头,而且取笑说,冻死报纸会说是走火入魔了自杀。
山东省潍坊军埠口镇杨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刘云香,经历过这样的迫害: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一日,军埠口镇原政法委书记花光勇等恶徒,把法轮功学员集中到军埠口大队酷刑折磨。当时正是严冬,恶徒们强迫男学员光着背,女学员穿着秋衣,光着脚扫雪,然后在雪堆中站着。先是拳打脚踢,皮管子打断了换上三角带再打。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山东省平度市祝沟镇八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当地政府。当晚政府副书记王永瑞强迫郑全花、王有忠脱下棉衣、光着脚、双手伸在雪里蹲了四十分钟(雪埋到脚脖处)。半夜十二点司法所的小潘又让郑全花只穿秋衣光脚蹲在雪里一个小时,还用小条抽打。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四,山东省沂水县法轮功学员李明艳、苏莉、相桂英、高玉梅去北京证实大法。后被劫持回来,非法关押在城郊洗脑班。沂水镇政法委书记何法江指使恶徒王建军逼迫李明艳、苏莉、相桂英、高玉梅、张军娥五人坐在雪地上。如果雪被坐化了,再提来凉水泼上,逼她们坐在雪水里,棉裤浸透了,人冻僵了。每天从晚上六点到凌晨四点,就这样连续折磨了四天。连张军娥来了例假也不放过,只见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冰雪,令人心寒,惨不忍睹。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多钟,被绑架在榆树市拘留所的任春英、刘淑娟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在炼功时,恶警孙景富、张福学等暴徒手持凶器闯了进来。他们把法轮功学员的外衣扒掉,按倒在湿板铺上毒打,每打一下,被打的人都哆嗦一下,毒打了约两个多小时,恶警都累得喘不上气。打完,又扔到外面雪地里冻(大约零下二十几度)。法轮功学员朱峰、柴秀芝被冻昏。大家往屋里抬,恶警却不让,扬言冻死她们,恶警许久飞说:“不许抬,拘留所每年都有三个打死的指标呢,怕啥,打死白打。”眼看几个伤重的人都要冻昏过去了,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恶警才允许把她们抬回屋。其中,有位女学员来例假了,仍遭张福学等恶警毒打,被扔到外面雪地里冻。恶警孙景富逼迫法轮功学员孙中芝脱掉外裤,孙中芝不脱,说来例假了,孙景富却说“这里没假”,照样毒打。恶警焦淑侠往背经文的女学员身上浇凉水,棉衣裤全湿透。恶警高永还把一位十八岁姑娘脱掉外衣扔到雪地里冻,姑娘的手冻肿得老高……
一九九九年冬天,地上很厚的积雪,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的恶警,在看守所叫犯人把山东乡男法轮功学员王某叫到院外,脱下裤子,只剩下裤头。恶人李立用脚在他臀部上踩了踩,然后狠狠的打了下去,皮条带着血弹了起来,一条大口子冒出了鲜血,接着二下、三下,三条大口子留在了臀部上。
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五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庆香女士,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被绑架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一次,一小队队长张国荣带领一帮犯人把刘庆香等十三位法轮功学员带到晾衣场,并将她们的衣裤强行扒下,只剩下内衣内裤。随后强迫这一群法轮功学员坐在厚厚的冰雪上,不许起来。刘庆香的内裤被冰雪融湿后冻在下身,寒冷无比。
在重庆永川监狱,二零一零年的整个冬天,狱警逼迫赖云昌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冰天雪地里正坐。下雪天,身上就会积很厚的雪。偶尔打了瞌睡,恶警指使服刑人员马光平,用燃着的烟头烫赖云昌的眼睛。要是没坐正时,还进行拳打脚踢,情景惨不忍睹。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城建工程学校教员张剑,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建华区北大街派出所绑架。派出所所长于志强带领一伙警察将他绑架到建华区建筑开发公司一间偏僻的办公室。他这样自述:“室内设有几张上下铺的铁床。他们五人将我双手反铐在上铺的栏杆上,双脚抻到对面铁床的栏杆上,于志强用脚踹使我的身体悠起来,我顿时疼痛难忍浑身汗水透湿,无知觉。他们又将我放到水泥地上,用茶杯盖的钮往肋骨缝里顶、拧、搓,又取来电棍发疯似的电击心脏、乳房、小便、腋下,我被电的大汗淋漓时,他们又将我的衣服剥光,只剩裤衩,把我推到户外的雪堆里,再往我身上浇凉水,在刺骨的寒风中,我冻的浑身颤抖、麻木、僵滞,致使我双臂四十多天不能动。”
二零零四年年初,大连南关岭监狱的狱警逼迫丹东市法轮功学员郑志强放弃信仰,施用了多种酷刑。晚上六点至七点逼他赤脚站在雪地里,并将一块约十五公斤重的牌子用细铁丝强行挂在他脖子上,如此迫害了十七天。同年四月四日,郑志强被迫害致死,年仅三十七岁。
堆雪人
在河北保定高阳劳教所,恶警逼法轮功学员坐在雪地上,然后用雪把人埋住,只剩头部。这种酷刑在哈尔滨女子监狱也被使用。有一位六十岁的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被扒得只剩内衣内裤,被刑事犯埋在雪堆里,只露脑袋。
雪埋活人
二零零一年的皇历大年初二,河北省雄县十里铺村农妇叶大俊,到北京上访,被警察绑架后,送到密云县迫害。在那里,恶人将法轮功学员衣服剥下,只穿秋衣秋裤,逼人趴在雪地上。然后两个恶人就用雪埋人,连头一起埋,一边埋一边用脚踩,有的被埋的喘不上气来,有的冻的脸青紫。叶大俊被埋了两个多小时。
二零零一年元月,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法轮功学员陈爱忠,与全家一块到北京上访。陈爱忠先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七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 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铐在院内一棵树上,将他的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寒冷异常,脚部的温度将脚下的冰雪化成了两个水坑。他的腿、脚早已麻木,严重冻伤。
后来恶警又把陈爱忠劫持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面对伤痕累累的陈爱忠,看守所恶警继续严刑逼供。恶警唆使犯人将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将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这次,陈爱忠被埋在雪中三、四个小时。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七日下午,河北省新乐市公安局副局长、“六一零办公室”主任白晚生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冬里,强令四名法轮功男学员脱光衣服,只穿裤衩,趴在新乐市看守所南墙根下的雪堆上,命令犯人张×× 拿铁铲把四名大法学员用雪埋上,先后用脸盆、水管往学员身上、脸上浇水。随后,他又逼法轮功女学员只穿小背心、小裤衩躺在雪地上,用雪埋,也是一盆一盆地往她们身上浇冷水。
一位福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三日晚上被绑架到北京海淀区清河派出所。为了逼他说出姓名,以李军威为首的恶警对他施以酷刑。他自述说:“最后屋里有五、六个警察,他们把我拉到屋外,扔到雪地里,全身盖上雪,我被冻得全身发抖。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他们把我拖回屋内,插上电炉,开起风扇给我吹热风。到了我全身快解冻的时候,他们就关掉电炉,给我吹凉风。这样折腾了四、五回,我感到全身疲软、麻木。……折腾到了半夜一点钟,他们觉得太晚了,就都走了,留下李军威和另一个警察。又把我扔到雪地里,盖上雪,找了一暖瓶开水浇我的头。他们看着表冻我半个钟头,才让我穿上衣服,把我铐在值班室的暖气管上。我这才慢慢恢复了身体的知觉,发现全身皮开肉绽,很多部位都肿痛得厉害。我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感觉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
为什么在将人要冻僵的时候再给人吹热风、浇开水?表面看是为了更残酷的折磨法轮功学员,可是很多北方人都知道,这样的折磨极易使人落下残疾。后面我们还将介绍恶警利用这种方式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残的情况。
坐冰
在吉林长春铁北看守所,零下二十多度的三九天,恶警在地上泼一层水结成冰,逼法轮功学员光脚坐在上面一天。好几个女学员来了月经,也被迫坐冰上,恶警根本不管不顾。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三,在河南开封北郊拘留所,夜间零下十度,滴水成冰。看守在院子的水泥地上倒水成冰,然后逼迫十一名女法轮功学员只穿内衣内裤赤脚坐在冰上或者雪地里炼功。手托冰块,头顶冰块。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坐到夜间十二点多,厚厚的冰地上留着三位来例假女学员一滩滩冻结的血迹。时隔几日,冰上法轮功学员坐过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
趴冰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看守所,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天还没亮,副所长赵才大声的喊一个犯人的名字,说打桶凉水来,又叫把水泼在院内地上。由于天很冷,院内又是水泥地,水泼在地上迅速冻成冰。这时,赵才说:你们不是炼法轮功吗?今天都给我趴在冰上。强迫十几个衣着单薄的女法轮功学员趴在冰上。
恶警逼法轮功学员趴冰还要求姿势:手臂向上、腿向下伸直,手心、脚背、脸部都挨冰,如哪处挨不上,恶警就用皮鞋上去踩,用皮条抽打。
法轮功学员把整个冰融化成一个人形,起来后手、脚、脸冻得肿起很高,变成紫黑色。这样一直趴到早晨开饭,冻得趴冰的人手都变成白纸色,才叫起来。吃完饭换班时,接班的警察看见院中冰上都是一排整齐的手形,不知怎么回事,一问才知原来是法轮功学员用手把冰捂化后产生的手印儿,恶警们却哄笑取乐。
自那以后,冬天院内经常有法轮功学员被迫趴冰,一趴就是几个小时。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所长王金将三号、四号屋内炼功的女学员拉到外面一起趴冰,一直趴了四个多小时。看见谁的手先被冻得失去知觉、变形后,恶警就穿着皮鞋狠狠踩手,起来后又把每人打的当场晕倒在地。把法轮功学员吕海利的头发拽下一大绺,并将正在来例假的法轮功学员张爱英剥下衣服,扯下内裤,狠劲的抽打。还有一学员被四个恶人踩住头和脚,两恶警用锹把儿粗的大棍子毒打致昏迷。
这种酷刑非常残忍。有时法轮功学员在外边承受过去了,可是回到屋里,一暖和,手钻心的疼,一个个的抱着手疼得掉泪。法轮功学员毛春平的手冻得失去了知觉,王金用鞋踩着她的手。回到屋里几天后,毛春平的手整个脱掉了一个黑壳。
冰块塞进衣服里
河北保定市江城乡法轮功学员李顺利,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六上午,在北京金水桥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被恶警绑架到北京顺义区南彩派出所。他自述说:“第二天傍晚,他们把我推到外面,双手背铐在外面的铁柱子上,在我脖子后面、腰上两边各放一块冰块,把我衣服拉锁拉开,用塑料桶给我脖子里灌了两桶冷水,上身、毛衣都冻上了,我把嘴咬出血。过了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屋里,用电棍电。当时冻的我全身哆嗦,一恶警三次用脚踩到手铐上。”
二零零二年冬天,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的恶警,指使刑事犯看着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如蹲不住昏倒在地,或稍动弹一下,就会招来谩骂和毒打。恶徒还把室内的窗户打开,把早已冻好的冰块,塞进法轮功学员只穿线衣的后背,让冰块慢慢地溶化。法轮功学员魏郡、朴英杰、高淑彦、丁洪娟、李洪霞,都遭受了这种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吉林省德惠市国保大队恶警绑架了武鑫宁、王长英、刘丙奇、刘德才、张守平等三十余名大法弟子。刘丙奇和刘德才被酷刑迫害摧残,恶警们将二人绑在了外面的树上冷冻,往裤裆内放冰溜子,手段残忍,全无人性。
残酷的冻刑让人生不如死,那它对法轮功学员造成的后果又该是多么严重呢?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有冻伤的经历。在寒冷的冬天,冻伤手脚、冻伤耳朵,那都是很常见的。而冻刑给人造成的伤害可就严重多了,甚至能将人冻残冻死!
冻疮
大连开发区医院的护士周艳波,于二零零零年十月被绑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先后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沈阳张士劳教所、沈阳沈新劳教所、大北监狱、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迫害。她为什么转了那么多地方啊?这就是中共内部邪恶的规定。如果哪个法轮功学员没在酷刑下屈服,仍然坚定自己信仰的时候,中共就将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加重迫害。这样“换监”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新一轮的摧残。周艳波经历的酷刑异常残酷。在她自述这段遭遇的时候,她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是有一个细节却让我们震惊。她说:“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那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盛夏的季节我的双脚都是冻疮。”
八月十日,已经都立秋了,可她脚上的冻疮还没有好……
冻掉指甲、脚趾
二零零零年二、三月份,在吉林省榆树市拘留所,十来个法轮功学员被逼迫从下午一点到五点站在雪地里,扒掉外面穿的棉衣,迎着刺骨的寒风,一站就是一下午,最后到吃晚饭时,才让回号房。当时,榆树市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任春英,十个手指全被冻白,手失去知觉。在拘留所期间十个手指全脱层皮,当从拘留所出来后十指甲全都被冻脱掉了。
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的贾海英,是个个体工商户,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她被绑架到图牧吉劳教所。一九九九年的冬天,图牧吉劳教所恶警逼她捡拾操场上的玉米粒。玉米粒跟冰雪冻在一起,就得用手抠,又没有手套,就只能用手指去抠,每天必须抠一小盆,否则就不让进屋。哪有那么多玉米粒子啊?!半个小时兴许能捡到一粒。七天后,贾海英双手的手指甲全部发黑脱落,手指头肿胀粗大,脚也冻坏了,脚趾发黑,发痒刺痛。
在滴水成冰的季节,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看守所恶警们在半夜三点多钟强迫几十名大法学员起床,不让穿棉衣,只穿秋衣秋裤,顶着刺骨的寒风光着脚绕着看守所大院一圈一圈的跑。当学员跑的体力不支的时候,恶警又在地上泼上水,水很快结冰,强迫大法弟子光脚在冰上长时间站立。丛培兰女士回忆说:“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那天是黄历腊月初七,一年中最寒冷的一天。刚下完雪,元宝山看守所所长张海清就把我们十名大法学员喊出去,让学狗爬,在院子里绕圈爬了近三圈。四个犯人穿着大衣,棉皮鞋轮班看着我们爬,他们还冻得乱跺脚。而我只穿了一件薄秋衣,一条薄绒裤,十个手指冻僵了,落地时能听到巴巴的响声,一会儿十指全部冻死。进屋后几分钟,手指盖就与肉分离。三天后,手指皮陆续往下掉,有的一块一块下来,有的整个一个手指筒掉下来,黄色的水不断往下滴,手指盖相继脱落。腿磨出血,裤子上粘着厚厚的一层皮肉,脱都脱不下来了。手都这样了,第二天警察还故意拿衣服来让法轮功学员(用手)洗。”
我们前文提到的河南禹州市法轮功学员尚水池,在被铁路工人救下后,他的大儿子找到了他。可是此时他已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两条小腿肿得很粗,毛裤都脱不下来。两只脚底板全部发黑发硬,十只脚趾头全部发黑发硬。后来回到家中,他的十个脚趾的肉全都烂掉,脚趾骨头脱掉了一节。
冷冻致子宫脱垂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境内新华农场法轮功学员宋慧兰,被劫持到汤原县看守所。看守所所长闫勇对宋慧兰说:“宋慧兰,你又回来了,你还想像上次那样绝食出去,你死了这份心吧,没门。”在晚上零下二三十度的情况下,他让宋慧兰睡在冰冷的地铺上,只盖着薄得透亮的被褥。宋慧兰每晚被冻得浑身发抖,以至造成子宫脱垂,鲜红的肉从阴部垂下,夹在两腿之间,非常痛苦。
冷冻致残
二零零一年元月十二日晚,济南法轮功学员徐法月(山东矿院九七届学生)被绑架,十三日下午被劫持到刘长山看守所。徐法月被紧铐成“大”字形,大小便一律在床上。在零下十几度的监号里,恶警开门冻他,刺骨的寒风令其裸露在外的手脚失去了知觉……五天后,他的手肿得像馒头一样,呈紫黑色,脚无知觉,无温度。右脚趾一、三、五均变为黑色,狱医、狱警怕担责任,将其送至警官总医院(又称劳改局医院),鉴定为左足、右手为两度冻伤、右足三度冻伤,一三五脚趾坏死。发出浓烈的恶臭。虽然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最终大脚趾被部分切除,三脚趾彻底切除,小脚趾部分切除,造成终生残疾。
邯郸市锦航绒布厂法轮功学员杨宝春,被迫害时年仅三十岁。二零零零年冬天,邯郸劳教所恶警以杨宝春坚持炼功为由把他的棉鞋扔到房上,让他光着脚站在雪地上。回屋后恶警有意用热水给他烫脚,使杨宝春的脚冻伤加上烫伤,很快严重溃烂。后来溃烂面积越来越大,恶警才把他送到邯郸纺织局医院救治,终因伤势蔓延危及到生命,杨宝春被迫截去右腿,造成终身残疾。
我们前文已经提到,人被冻伤后,被冻伤的地方是不能立即用高温暖或用热水烫的,得逐渐慢慢的恢复。恶警为什么要用热水给杨宝春烫脚?用意非常阴险,就是要使他的双脚残废掉。
冷冻致死
潍坊昌邑市宋庄镇三大丈村法轮功学员刘述春,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被劫持到昌乐劳教所二大队二中队。当天,二中队队长韩会月、二大队副队长朱伟乐,指使劳教犯刘春祥、张金涛、牛中新、田伟祥、刘学田、韩喜才将刘述春毒打一顿之后,再给其所谓“洗澡”。即长时间泡在水里,然后用笤帚疙瘩、拖把、棍子、小板凳等工具给所谓的“搓”,即往死里打,然后再用风扇吹,再一阵拳打脚踢。整个过程中不断的传出刘述春的痛苦喊叫声。刘述春当天就被折磨致死,年仅三十八岁。
大庆市采油六厂四矿材料员,家住大庆市让胡路区采油六厂何华江先生,于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多被劫持到大庆劳教所。当晚六点以后,在一楼洗漱间,犯人们开始邪恶的酷刑折磨何华江,扒掉衣服,把他绑在铁椅子上,嘴给封上,开着窗户,用水管子对他不停地浇凉水,中间有时还推到外面冻着,恶徒王庆林叫喊:“你写不写?你听没听见?……”副大队长张明柱咆哮着:“不要住手,给我浇!看你还炼不炼了,叫你知道我是谁”。
何华江痛苦的惨叫声,至深夜十一点多钟越来越小,最后连微弱的呻吟声都没了。何华江被虐杀停止了呼吸,悲惨的离开了人世,年仅四十二岁。
黑龙江省大庆市石化总厂建设公司筑炉公司职工许基善,被绑架到大庆红卫星监狱七监区。二零零五年六月七日,大庆监狱的十多名犯人上来将许基善的衣服扒光,并捆绑在用铺板绑好的十字架上,把嘴堵上,抬进厕所平放在地上,头冲北脚冲南。厕所内东北角有一条四寸粗的上水管,离地面约一米六、七处焊了一个放水的龙头,接有三、四米长四寸粗的黑管,他们就用这个水管往许基善的头部、身上浇水。从上午九点钟一直浇到下午一点钟,四个小时不停的向许基善身上猛哧。许基善颤抖着,呼吸困难,疼痛难忍,由于背着十字架,一动也动不了,痛苦中他将嘴唇咬破,并大喊:“救命!”可是暴行并没有停止,直至被活活浇死。现场看到,许基善光着青紫的身子,口中、鼻腔内有血块,嘴角全都咬坏了,肚子已经灌满了水,胀的老大。
冻刑带给受难者的痛苦远非我们的文字所能承载。冻刑虽说从古就有,可从没有达到今天中共暴徒使用这种酷刑的规模和摧残程度,而且它针对的还是一群只为做好人的修炼人。中共不解体,这样的酷刑就不可能被终止,它还可能被施加到其他的中国人身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