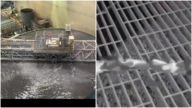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天就开始了越权行为。这与近代历史上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和国会民主党占多数的时候都有相同之处。只要给他们最微弱的选举胜利,他们就会急不可耐的插手州一层次的事务。
共和党州政府官员正在谈论如何回应,就像他们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做的那样:利用州权进行对抗。
各州对抗联邦政府的方式,其正确名称是干预(interposition) 。(美国第四任总统、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首先将这个词应用于州宪法对联邦权的审核,我们的宪法制度中包含了干预这一方法。
我已经为州政府官员提供了近30年的有关干预的建议。2016年,我在哈特兰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本文总结了此论文的一些结论,并补充了进一步的观察。
干预的方法涵盖从很弱到最强的宪法途径,有些方法有重叠之处,州官员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或全部方法。但是,有些形式并不总是有效,有些会适得其反。
教育方法
一种教育手段是通过州立法决议,谴责联邦政府在某些方面的越权行为。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有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第十修正案决议》。1994年在科罗拉多州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包括以下文字:
“依法解决……科罗拉多州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声明州的主权超越所有未经美国宪法列举和授予给联邦政府的权利。”
“本决议将通知和要求联邦政府,作为我们的代理人,应停止和终止任何超出宪法授权范围的权力,此指示立即生效。”
这种“通知和要求”没有威慑力,联邦官员不予理睬。
有时甚至州政府官员也会忽视立法决议。2011年,蒙大拿州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反对“真实身份法”的决议。蒙大拿州的行政部门则继续推行这个计划,立法机构最终让步了。
我相信仅仅通过决议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它们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也应体现在更有效的措施中。
游说国会
州立法决议就联邦制度问题,照会国会是游说的一种形式,但国会基本上把这类决议扔到废纸篓里。
1995年,密歇根州州长约翰·恩格勒(John Engler)以更个人化的方式游说。他在国会游说团安营扎寨,推动一项遏制联邦法令的法案,他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那是26年前的事了,当时共和党在国会是多数党,急于缩减联邦的过度开支。
我不认为今天的州游说工作有多大价值,也许除了在缓和无论如何都会通过的糟糕立法方面。
司法挑战
近年来,各州已多次起诉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胜利可能是说服最高法院以7比2的多数票,否决了奥巴马医改要求所有州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法令。
经过深思熟虑的司法挑战往往值得花费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样的胜利很少,而且范围往往很窄。
诉讼可能非常耗时。最高法院支持奥巴马医改的其余部分,只是因为它得到了旨在迫使公民购买政府批准的医疗保险的“税收”的支持。然而国会在四年前废除了这项“税收”,按照最高法院的逻辑,奥巴马医改应该已经崩溃了。但诉讼仍在继续,联邦政府继续把奥巴马医改强加给我们──推高了成本,将动脉硬化扩散到整个医疗系统,并剥夺各州和家庭的医疗保健自由。
各州间的协调
州际协调由来已久,久经考验,而且是真实的:第一次美国殖民地会议于1677年举行,最近一次的州际会议于2017年召开,一共举行了大约40次。
其基本程序是:一个州号召开会,审议一个共同的问题,其他州同意参加,各州派代表团开会,审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阴谋论者就以似是而非、往往荒谬可笑的理由攻击州际大会 。例如,1994年至1995年,内布拉斯加州民主党籍州长本·尼尔森(Ben Nelson)和犹他州共和党籍州长迈克·莱维特(Mike Leavitt)提议召开一次非正式的“州际会议”,探讨对联邦法令的共同回应。阴谋论者声称提议的会议可能会变成“制宪会议”,可能会发生政变!尽管他们的说法很荒谬,但它给了对此不感兴趣的许多州的立法者一个逃避参与的借口。
幸运的是,在如今的电话会议时代,通常不再需要亲自协商(除非为了修宪,见下文)。此外,几个全国性的州政府官员组织定期开会,以促进沟通。这些组织包括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 (ALEC) 和全国州立法机构会议(NCSL)。
宪法修正案
到1787年,“州际会议”的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国父们将其写入宪法,作为正式向各州提交宪法修正案以获得批准的一种方式。会议机制允许占绝对多数的州在没有联邦批准的情况下修改宪法,这是联邦制度的核心“制衡”,很像总统的否决权,但更重要。
与所有国父们的期望相反,这种机制从未被使用过。当然,这也是联邦政府现在功能失调、过度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该程序仍然可用,而且大多数州的立法机构 (但不是必要的三分之二) 已经批准了会议决议。
不合作
正如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最高法院的非强制性原则认为,联邦政府一般不可以命令州政府做事情。各州可以拒绝与联邦项目合作,或拒绝执行违宪的联邦法律。但这并不妨碍联邦政府本身实施其计划或执行其法律。
然而,如果一个州接受联邦资助,中央政府可以要求该州遵守该项目的条件。例如,国会可能不会命令一个州将饮酒的最低年龄提高到21岁,但它可以用21岁的州饮酒年龄作为获取联邦公路基金的条件,来完成同样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一直建议各州拒绝接受以下的联邦拨款:(1) 过于侵犯州与联邦之间的平衡;(2) 产生破坏性的效果或造成其他损害。
这里有一个关于州政府不合作的讽刺故事。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保守派议员经常提出不与违宪的联邦项目合作的建议。左翼政客和媒体经常指责他们是“极端分子”和“宣布无效分子”。
但是最近,左派控制的州和地方政府停止了明显符合宪法的联邦项目──移民控制。突然间,不合作不再是“极端”的,而是“人道”。
立法者考虑不合作时须考虑州行政部门的态度。1995年,蒙大拿州的立法者通过了一项“反授权”法令,要求行政部门定期审查联邦法令,评估其对该州的影响,并提出减轻影响的建议。行政部门基本上忽视了这一法令。
宣布无法律效力
宣布无法律效力至少有三个含义。
第一:传统和最精确的意思是:颁布一项州法律或州公约条例,宣布联邦措施在州内无效。
这种形式的无效没有宪法价值,尽管偶尔有相反的主张。詹姆斯·麦迪逊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阻断形式。(该法案的提出者托马斯·杰斐逊和主要发起人约翰·卡尔霍恩,严格的说都不是宪法学者。)
传统的宣布无法律效力的方法过于笨拙,无法处理多个联邦行动,而且尝试使用它的努力通常很快就会消失。此外,宣布无法律效力这个词也带有政治色彩,无论公平与否,它在公众心目中,都与南方奴隶主在南北战争前的立场有关。
第二:发言者有时会使用宣布无法律效力来表示“各类干预”(“interposition of all types.” )。我强烈反对这种用法,一是由于其不精确性,二是由于该词的历史包袱。
第三:这个词是对各州无视联邦法律,而采取的超越不合作的肯定性行动的不准确描述。近期最著名的例子是大麻在各州的“合法化”。
确切地说,一个州不能使大麻合法化。无论州政府怎么做,根据最高法院通过的联邦法律,这种物质仍然是非法的。(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的意见不算数。)
的确,在非强制原则下,各州可以废除他们自己的反大麻法规。这是不合作的合理形式。但是许多州已经超出了废除的范围,它们通过了法规授权,建立广泛的大麻分销和管理网络的法规,州财政收入甚至来自于大麻销售。
严格来说,这些州参与了一场犯罪阴谋。他们之所以逍遥法外,是因为大麻合法化是左派最喜欢的事情。保守州是否能在其他领域采取同样的措施仍未可知。
作为一个有执照的律师,我不建议藐视联邦法律。但一些州可能会决定这么做。例如,一个州可以对抗奥巴马医改,通过“合法化”和坚决支持奥巴马医改声称禁止的自由市场医疗保健选项。
每个州都必须自行决定自己喜欢的干预方法。为了应对媒体的敌意,官员必须经常提醒其选民,干预是我们宪法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制衡手段。
原文:How States Should Push Back Agains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罗伯特G·纳特尔森(Robert G. Natelson)是著名的宪法学者,退休前担任宪法学教授,现任丹佛独立研究所宪法学高级研究员。他也是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成员,并长期就联邦制问题向州立法者提供建议,著有《原始宪法:它实际上说了什么和意味着什么》(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at It Actually Said and Meant)(2014年第3版)一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