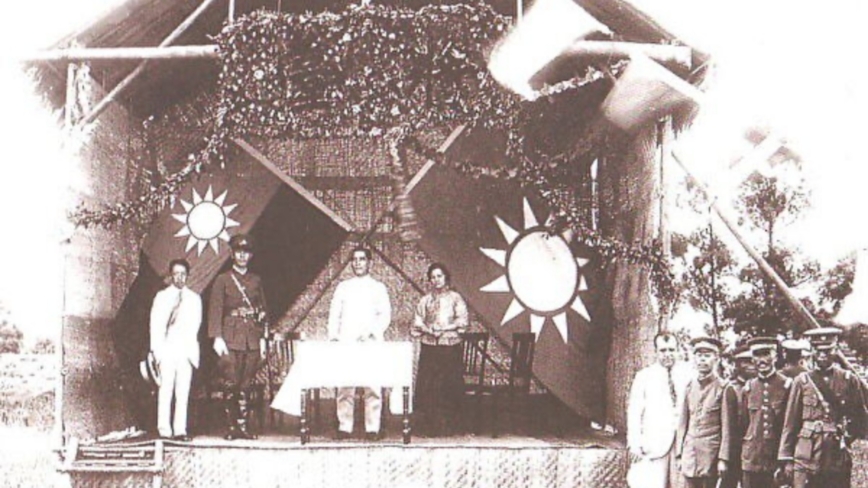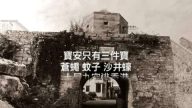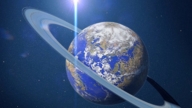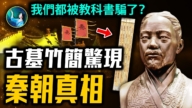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时间2025年05月08日讯】接上文
三、中共是怎么壮大发展起来的呢?
苏联不仅为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壮大提供了必须的资金,而且通过与孙中山结盟,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机遇。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了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制定了“联俄容共”政策。苏联愿意结盟,图的是什么?从近期说,是影响、左右国民党的政治倾向和方针政策;从长远着眼,则是“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最终在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组织。
如何实现这两大目标?苏联的办法就是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从而监督、改造国民党,并争取取而代之。
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马林建议让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工作。孙中山接受了这一建议。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强调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批准了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该会议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次大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
国共合作前,国民党已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而中共只是一个党员人数不足200人的小党。通过国共合作,中共得以成功附体国民党,迅速发展壮大,逐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那么中共是怎么通过国共合作附体国民党,发展壮大起来的?
首先,中共凭借苏联对国民党的巨大影响,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内包括国民党高层的相当一部分权力,政治资源大为增加。
据杨奎松教授研究,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的人数虽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大约3%,出席一大的人数却已占到大会代表总人数的10%左右了。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中共党员所占人数达到了全体委员的大约25%,即将近1/4。而在大会后产生的国民党权力机关中央党部的7个部中,中共党员又占据了2个部长和3个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的席位,并且在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占据了1/3的发言权。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身份,共产党方面在国民党决策层中,自然就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力量。
另外,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诸如直隶、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山西等许多全国重要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组建工作先后也都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从而使地方党部均为共产党人或亲共左翼人士所掌握。就连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部分国民党支部,也为共产党人所左右。(注11)
到了国民党二大,中共的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上升。这次大会,从议程到决议内容都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不但占了出席代表的一半以上,而且在中央党部的八部一处中,中共人员竟占据了77%左右的领导职位,从而控制了国民党的几乎全部实际工作。另外,国民党一大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共52名,中共党员占10名,不足1/5;二大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共80名,中共党员占19名,约占1/4。一大后在中央党部中,中共党员仅5人,不足1/4;二大后中共党员占到17人,约占77%。(注12)
其次,由于通过国共合作,中共在国民党内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它的政治能量自然也就大大增强了,也就有充足的条件开展活动了。于是我们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26年5月初,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十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
以农民运动为例。国民党一大闭幕后,成立了有共产党人林伯渠、彭湃、阮啸仙、罗绮园、周其鉴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林伯渠任首任农民部长。随后又成立了农民部下设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林伯渠、毛泽东等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席。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是专门负责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机构,这两个部门在推动农民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共产党控制了这两个要害部门,等于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农民运动。
国民党一大后,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这两个部门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了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发起农民运动。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鼓动农民起来造反,跟地主乡绅展开斗争。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21万多人。北伐战争前夕,广东省乡一级的农民协会增加到4700多个,会员增加到70万人。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了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了七百多名农运骨干,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说:这些农运骨干“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
再有很重要的一点,中共还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机遇,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和干部,并将触角伸入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到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中,中共党员已达上百人,其第一、二、三、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三个师中两个师的党代表,九个团中七个团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人。
为了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和干部,中共选派了大批党员和左翼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校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积极发展党员。
1924年秋冬间,中共黄埔军校支部成立,隶属于中共广州地执委,后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1926年3月,中共黄埔军校支部又扩大为特别支部。中共还通过秘密方式在军校学员中逐步发展党员。到1926年北伐前,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数量已达到几百人。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多,中共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多个党小组,如中共黄埔军校步兵科党小组等,以加强党员之间的联系和组织管理。中共还在黄埔军校创办了《红色周报》和《红色周刊》等党刊,通过这些刊物向军校师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利用国共合作的机遇,中共还拥有了第一支自己的正规武装——叶挺独立团。该团名义上归国民革命军第4军建制,实际上完全由中共掌控,团长、营长和骨干都是中共党员,部队内建立了党支部,下辖6个党小组。这也是中共在军队中设立的首个基层党组织。党支部初期约有20个党员,不属第4军政治部管,属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直接领导,请示汇报工作找周恩来,周恩来不在广州时,就直接找陈延年。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一举成名,后成为中共南昌起义的骨干。
综上所述,国共合作前,中共只不过是一个人数不足两百的区区小党,但短短几年间,到国共合作破裂时,却已迅速崛起为一支不容小觑、足以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政治势力。如果没有苏联通过与孙中山结盟,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的机遇,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
四、中共是靠一己之力打败国民党的?
经过八年抗战,国民党元气大伤,中共实力大增,彼此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如此,在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无论是双方控制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还是拥有的经济资源,也无论是双方军队的数量、战斗力还是武器装备以及军工企业的规模,国民党方面仍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按蒋介石自己的分析:“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注13)正因为如此,不仅蒋对“剿灭共匪”充满信心,大部分国军将领也都乐观地认为,击败共军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如果有人说,几年后江山就会变色,共产党将夺取天下,没人会相信。
那么中共为何在实力远逊于国民党的情况下,短短几年就打败了国民党呢?它是完全依靠自身的一己之力取得胜利的吗?
历史表明,导致中共在内战取胜的原因并非单一,但苏联的援助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这种援助首先体现在苏联为中共抢占东北这个战略要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为什么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因为它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所以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取得东北,则华北华中即有了依靠,我党地位将为之一变”,故此为“决定的一环”。此后的历史也证明,中共之所以能在全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在东北取得了胜利。
对于东北的战略价值,蒋介石当然也心知肚明。所以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都急于抢占东北。当时东北掌握在苏军手中,按照中苏条约,苏军理应向国民政府移交东北的主权,但苏联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却为中共抢占东北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对国军进入东北设置各种障碍。
1945年10月1日,苏联大使正式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准备从东北撤退。仅仅两天之后,苏军将领便明确告知中共东北局称,中共中央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十分正确,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抽调主力25万到30万人,分别部署在山海关一带及沈阳附近,把住东大门,不让国军进入东北。有苏联撑腰,中共信心大增,毛泽东明确提出“竭尽全力,霸占东北”。
到1946年1月初,苏军又将辽阳、鞍山、本溪等地相继移交给中共。如此一来,这一有着上千万人口的东北重要工业区,自然就如愿以偿地落入到了中共手中。随后,苏军相继从抚顺和沈阳撤走,不仅不向国民党办交接,而且通知中共东北局,准备在其撤退时大量接受各地政权和厂矿企业。
在苏军的援助下,到1946年6月,中共抢进东北的部队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收编了数十万原汉奸军队,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而且控制了相当一部分东北地区,为此后进一步壮大发展中共在东北的力量,直至取得在关外与国军决战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在为中共抢占东北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苏联还对中共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尤其是在武器弹药和建立军工企业方面。
中共对外一直宣称,“中国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中共手中的美式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这完全是在说谎。
1945年8月,中共最早派往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总兵力仅11万人,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甚至有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来到东北的。但仅仅用了3年时间,中共在东北军队就迅速发展成了装备精良、人数百万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如此,不是因为中共自己有多大本事,而是因为苏联源源不断地为它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还为它建立了强大的军工企业。
日本一投降,苏联就向中共移交了东北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弹药。
中共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是最早一批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苏军向他们转交了苏家屯的关东军武器库,“向外拉了三天武器。一次一下就拉了20个车皮的武器,共2万余支步枪,一百多门大炮,二十多万发子弹。”曾克林部力量因此迅速扩充。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致电中共中央说:“曾克林部原一千五百人,现共发展到三万七千人,轻重机枪约四百挺及相当数量的子弹。”
1947年,苏联还将其在东北控制下的重工业工厂全部移交给中共。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以民用企业建新公司的名义,在大连成立了当时东北最大的军工企业,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不仅建新公司包括的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几个大连主要的重工业工厂,都是苏军转交给中共的,建新公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援。这家公司投产后,不光为东北共军,也为华东共军提供了大量的炮弹和其它军事物资援助。从1948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钢质炮弹,由海上运输,源源不绝地供应华东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期间,大连兵工厂输送到淮海前线并投入使用的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可见,在苏军支持下的大连军工企业,为中共赢得淮海战役和全国的胜利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
1948年,正值国共决战的关键时期,苏联不仅继续向中共军队提供了大批日本关东军武器,还援助了大量本国和捷克制造的先进武器。特别是大量飞机、大炮、汽车、坦克、炮弹等重型武器的援助,一举让一直以来在武器装备上都严重落后于国军的共军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进。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统计为: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枪385,134支,短枪50,352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六零炮2,890门,迫击炮986门,山炮324门,野炮194门,榴弹炮92门。除重炮外,从数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势,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由此可见,在苏联援助下中共东北野战军实力增长之快,这也正是中共将“三大战役”的开启选择在东北的原因所在。
根据杨奎松教授披露的苏联政府解密档案公布的数据,在国共内战期间,苏联提供给中共的武器弹药主要包括:
1. 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 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的130亿美元武器中的40亿美元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 而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反观国民党方面,内战爆发后,1946年7月,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禁运,一直到1948年11月才正式解除,而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
不难想像,如此一来,国共的力量对比不能不迅速发生逆转。以华东野战军八纵队为例。该纵队下辖3个师,炮兵团、新兵团各1个;69团的3个步兵营中,1个全日械,1个捷克式装备,1个全美式装备;每连9挺轻机枪,每营1个机炮连,3门迫击炮,6挺重机枪。连长有挑夫,营长有马骑,火力与国军主力不相上下。故陈毅当时才会底气十足地说:“现在我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国民党差,也不比抗战时期日寇差。”
国民党在1949年联合国第四届大会上指控的一点不错:苏联撤军时把东北交给中共(仅把一些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为中共打开了一条从华北自由进入东北的通道;把近百万日军装备及军事技术悉数转交给了中共;与中共签定了一系列提供物资、技术和其它援助的协议和合同。
可见,没有苏联的这种大规模援助,中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和“小米加步枪”,是根本不可能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就像杨奎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注14)“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注15)
终上所述,无论是中共的建立还是生存,也无论是它的发展壮大还是夺权建政,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跟苏联息息相关。历史确凿无疑地表明,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夺权成功,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共产极权,是俄共有目地有计划的“输出革命”,培植和豢养反华势力中共,千方百计插手和干预中国事务的结果,也是中共卖身投靠俄共,在苏联的帮助下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共执政既不是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共产极权也不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苏联在中国蓄意培植的怪胎。这个怪胎理应也迟早会被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土地上清除!
注释:
(注1)叶永烈《红色的起点》
(注2)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
(注3)周佛海《往矣集》
(注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注5)张国焘《我的回忆》
(注6)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原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注7)网文《两个局外者的对谈》
(注8)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注9)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2页
(注10)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
(注11)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75页
(注1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注13)《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135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注1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注15)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