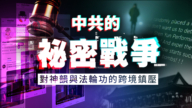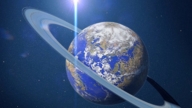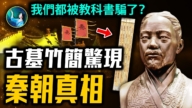2025年6月23日,中共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强调“黄金兼具商品与货币双重属性”,称其对“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方案表面是为了推动产业升级,实则旨在提升黄金在中国金融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暗示政策重心已由“产业安全”转向“金融稳定”。
2025年初,黄金价格从2,641美元/盎司飙升至3,509美元/盎司,涨幅32.9%,成为最稳健的“资产避险港”。全球央行2024年增持超1,000吨黄金,占储备资产20%,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两倍。在全球央行纷纷增持黄金、美元信用逐步下滑背景下,黄金已脱离纯粹商品属性晋升为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无主权信用资产”。
中共此次推出黄金产业新政策,正是在中美关税战美元获取能力下降、货币超发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内外双重困境下,试图以“增产+扩储”方式,为稳定人民币预期而进行的“金融自救”。
中国黄金产业现实困境:产能第一,结构失衡
2024年,中国矿产金产量达377吨,连续18年全球第一。同期,中国黄金消费量为985吨,连续12年全球第一。中国黄金产业看似产消两旺,实则存在资源保障能力不足、工业用途偏低和企业竞争力差等诸多结构性问题。
第一、产量增长乏力:2024年中国黄金产量增幅仅0.56%,因传统产区老矿枯竭,新矿投产周期长,所以原料供应高度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为46.22%。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凭借更高资源储量和开采效率,正逐步缩小差距。
第二、工业用途偏低:超过九成消费集中在首饰和投资领域,真正用于高科技制造、电子信息、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等工业领域的比例不到10%。比如2024年985吨黄金消费量中,有54%用于首饰、38%用于投资,真正进入工业制造的不足8%。
第三、资源储量和品味偏低:大多数金矿为露天开采,品位在1~4g/t之间,即每吨矿石能提取1~4克黄金(而南非为9.38克)。探明储量3,100吨,仅占全球4.8%,远低于澳大利亚(1.2万吨)和南非(5,000吨),结合产量看可采年限仅15年(澳大利亚30年、南非40年)。
第四、产业“小散乱”问题严重:80%的矿山为中小企业,设备落后、环保事故频发,盈利能力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黄金集团净利润率为8.9%,对比国际企业差距明显(如澳大利亚纽蒙特矿业达25.77%)。
总的来看,中国虽在黄金生产和消费规模上处于领先优势,但整体产业结构仍处在价值链底端,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寥寥无几。
政策目标与意图:“产业升级”是幌子,“金融稳定”是核心
新政策勾勒出宏大愿景:资源储量增长5%~10%,产量提升5%以上;日处理矿石500吨以上的矿山占比达70%;突破深层矿产开采(2,000米以下)、无氰提金等关键技术。
然而,这些目标大多严重脱离现实。从资源储量和品味、技术水平到产业结构,中国黄金产业全面“欠账”,想要在三年内实现产能跃升与技术突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深部矿产勘探难度大,资源枯竭显着,新增储量增长面临较大压力。行业分析普遍认为,未来中国黄金储量增长将主要依靠提高勘探效率和开采技术,而非单纯依靠新增资源储量。
第二、传统产区(山东、河南)矿山年产量呈3%~5%下滑趋势,而新矿从勘探到全面投产,平均需要5至7年甚至更久,很难在短期内显着增长。2024年中国黄金产量377吨,仅比2023年增长2.1吨,几乎接近零增长。
第三、无氰提金技术作为解决氰化尾渣问题的源头性控制方案,尚处于实验室研究和试验阶段,提金率低、成本高。在全球范围内,无氰技术应用比例不到10%,尚未实现工业化大规模替代。
第四、深部开采(千米以上)安全性差、效率低,全国多地金矿(深井)事故频发,导致停产整顿。如湖南金矿连续发生矿难、山东金矿发生爆炸与火灾,多数为深部矿层作业。
第五、80%为中小型矿山(日处理<200吨),治理能力弱,频繁发生尾矿泄露、废水排放及重金属污染事件(如2024年贵州安顺、黔西南等多地严重矿山污染)。
此外,中小矿山整合还涉及地方利益冲突,早在2008年,紫金矿业整合当地小矿时,因为征地补偿问题与村民冲突升级,爆发了严重警民冲突,造成多人伤亡。
总的来说,黄金在中国工业需求占比低,产业升级经济贡献有限(2024年黄金产业对GDP贡献约0.72%)。但黄金兼具商品和货币属性,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地缘政治紧张时,是无可替代的避险资产。
因此,这次新政策的核心是金融安全战略延伸。所谓的“产业整合”,更像是为国企铺路的政治操作,而非经济效益驱动。借整合淘汰中小矿企之机,扩大国企在黄金资源和金融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为黄金“金融化”创造制度空间,弥补货币超发带来的“货币信用塌陷风险”。
中共金融维稳焦虑与黄金“救火”角色
2025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中美关税战升级、人民币贬值预期、外汇储备承压,促使中共不得不将黄金作为“硬通货”以对冲金融风险,稳定金融体系。当局对黄金产业政策的“紧急加码”,反映出其正面临严峻金融安全问题:
首先,货币超发与信用透支:2020—2024年中国M2年均增速维持在10%以上(最高11.81%),M2/GDP比值高达2.32(为创造1单位GDP要超发2.32单位货币),远超日本的1.97,货币泛滥严重。
2025年,当局已实施降准(50个基点,释放约1万亿人民币流动性)与降息(MLF利率降至2%),并推出超过10万亿财政刺激(包括赤字扩容和专项债)。
其次,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2025年,离岸人民币(CNH)一度跌至7.4287兑一美元,逼近历史低点,市场预期人民币可能进一步贬至7.45~7.8。中共央行通过设定每日中间价、2%交易区间、抛售美元和收紧离岸流动性管控汇率,但成本高昂。
2015—2016年类似干预耗费约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2025年外汇储备(3.3万亿美元)增长停滞,资本外流风险进一步放大。货币超发与贬值预期的恶性循环,使人民币稳定成为金融安全的首要挑战。
最后,中美关税战加剧外汇困境: 中美关税战自2018年开打,2025年进一步升级,目前美国对华关税升至55%。关税战直接削弱中国出口创汇能力,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5月中国对美出口暴跌34.5%,创下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
虽然中国通过贸易转移(如对越南、墨西哥出口)部分抵消影响,但欧盟、东盟等替代市场无法完全弥补美元收入损失。为节约外汇,中国压缩非必需品进口(如奢侈品),但能源、芯片等关键物资进口仍需大量美元,外汇储备压力持续加剧。
这“三重危机”迫使中共寻找替代策略以增强金融安全。在此背景下,黄金被赋予三大关键角色:
第一、对冲货币超发,稳定市场信心,缓解资本外流。货币超发导致人民币信用透支,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避险资产,可为央行信用背书,增强人民币币值稳定性。
第二、减少美元依赖,缓解外汇压力。中美关税战削弱美元收入,外储增长停滞,汇率干预成本高昂。黄金作为非美元资产,可部分替代美元储备功能,减轻干预压力。
第三、应对地缘风险。2025年,全球地缘冲突加剧(如乌克兰危机、中东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资产”,可在金融制裁或资本流动限制时提供缓冲。
官方数据显示,5月末中国黄金储备约2,296吨,占外汇储备7%,远低于全球央行15%的平均水平。新政策欲将黄金储备作为金融稳定的“最后防线”,但这样低比例的黄金储备抗金融风险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承担这个定位。因此,通过黄金来给中国金融“救火”更像是当局的一种心理安慰。
结语:黄金产业新政策或将引发金融失控
表面上,《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是一项产业政策,实质上却是中共央行对冲货币超发、稳定人民币信用的“隐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外汇储备增长乏力、美元收入受限、人民币贬值压力剧增背景下,黄金被提升为国家信用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以资源之名、应金融之需的政策转向。黄金不再只是矿业,而成为央行货币体系的“防火墙”。然而,中国高成本矿企(债务率超60%)和金价波动(2024年达20%)使得政策风险极高,一旦国际金价出现回调则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波及金融体系。
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黄金产业本身的短板,而是当局寄希望于黄金弥补整个货币信用体系裂缝的意图本身。若政策落空,央行“放水”的风险,就可能转化为一场系统性的金融失控。这场以“黄金”为名的博弈,注定充满变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