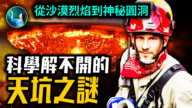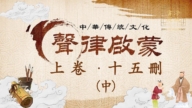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1月12日讯】(一)文革初期是恐怖的。
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造反派关进“牛棚”,整日揪斗,受尽非人的折磨。父亲偶尔被放回家,我与弟妹看到胡子拉碴、目光浑浊的他,都用胆怯的眼光盯着;心很痛,却不敢上前去与他说话。父亲从来严厉,他这样子,我们就只有更加敬畏和痛楚。
父亲不会喝酒,他接过母亲专门为他泡制的药酒,闷着声一口咽下,两道浓眉紧紧地蹙拢。再接过一杯,倒在手心,在四肢和身体上擦拭,他不经意间也咧咧嘴。看得出,他很疼痛,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瘀血和伤肿的痕迹。
母亲眼眶有些潮湿,她不让我们看父亲身上的伤。她平时也不准我们去看造反派们斗争“走资派”的场景。然而,母亲又怎能时时监控得了我们。学校已“停课闹革命”,我们一群不满十岁的“狗崽子”,没了去处,整天窝在小院子里,偶尔,也悄悄地去看批斗“走资派”。当然,斗自己父亲的场合是肯定不会去的。那天,在县人委大楼前围了数百人,正三呼着口号在斗争人。我从大人们的胯下挤了进去,见半圆形的十余级石梯上,呈九十度地弯着一个人,脸被血液胀得乌红,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滴。那人,是县委的监委书记,胸前挂着一块沉重的牌子,牌子上的名字被红笔大大地打了一个叉。猛然,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往监委书记的屁股上就是一脚。监委书记随即噗噗噜噜地直滚到了阶梯最下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莽汉说他装死,便几步跑下阶梯,大喝着又朝他一脚,见还无动静,就一把翻过身,试了试还有鼻息,对另外的人说,把老狗押回去!于是,有两人拽着监委书记的手,就地拖走。那拖痕下,有一丝血迹,那是他额头上的血。
我不知父亲是不是也这样被揪斗。心里,反正有一股怒火在燃烧;想到那恐怖而令人颤栗的场景,牙齿便咬得咯咯响,小小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攥得紧紧的。揪斗中被致残者,司空见惯。造反派手段残忍,酷刑也多,最常用的有坐喷气式飞机、点天灯、挂元宝、猴子望月、猴子看瓜……受不了这万般刑罚的,只有选择死亡。
那日子里,县城常常有自杀的。只要听说有自杀的,我们都要跑去看,虽然也毛骨悚然,毕竟县城太小,天性好奇的孩子实在经不住诱惑。印象中第一个自杀的,是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忍受不了,便在家中悬梁自尽。这人姓杨,家住中华路,也就是公安局路口左边第二家。此后,就像决堤的水,自缢者每三两个月就会发生。不少小伙伴的亲人,就这样凄惨地告别人世。幸好,家父没有走这一条路。
其实,父亲也在非人的折磨中产生了轻生自尽的念头。或许是母亲的挽留,或许是惦念未成年的孩子,他终于没有自尽。他未写完的遗书,我是在成年当兵以后才看到的。遗书是写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中。这本笔记本,是他在部队时的纪念品,封面是天蓝色的,精装硬壳,上面有毛主席的压模头像;父亲舍不得用,没有写过一个字,打算在我长大后留给我。再是舍不得用,他还是在里面写下了遗言,是用铅笔写的,时日长了,铅笔粉有些模糊。遗书也就百来个字,大意是:
孩子,我把家事告诉你。父亲姓甚名谁,祖籍在中原某处农村,祖辈都是贫苦农民。父于何年何月参军,参加了哪几个重大战役。部队转业后,现在何处工作……
没有写完,止笔了。我不知父亲当时的心情,也不知当时是不是寒冷而又漆黑的深夜。但我肯定知道,他很痛苦,眼前完全没有任何光亮与希望可言。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止笔,或许是母亲突然叫他,也许,是瓢泼大雨的夜暗里,突然有一道闪电划过夜空,让父亲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亮光,也许是惊雷震撼了他的心灵,他毅然停笔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让遗书意外中止,反正是一件幸事,否则,我在童年就失去了父爱。我的人生,也不知会是怎样的凄苦蹇舛。
(二)
父亲被关“牛棚”,我却常常跑到关“走资派”的“牛棚”那里去。就是想看到父亲,想看他慈祥的目光,想他用温暖的大手牵着我搂着我。每当他用他的大手牵我,就会感到一股暖流从手掌传遍全身,温暖也洋溢全身,更会感到融融的幸福。其实,也就是在这时候,才能稍稍地多得一点父爱的感受。
父亲平常总是忙忙碌碌,极少同我们说话,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和没有表情的脸庞,我们几姊妹常常是心生敬畏,想多同他说一句话也不敢。他当了“走资派”后,不忙了,可却又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天被折磨得疲惫与痛苦。有几天,造反派不斗他了,勒令他在家里写检查。他和几个“走资派”叔叔伯伯到家里来写。隆冬季节,天气格外寒冷,我们在家冷得瑟瑟发抖,为了节约,只在火盆里烧一小节木炭取暖。而父亲却将火盆加满了木炭,烧得红通通的,屋子里格外暖和。虽说暖和了,我幼小的心里,不忍心痛,为了另几个“走资派”叔叔伯伯不冷,家里要浪费多少木炭呀。父亲似乎一点也看不出我们的心思,他的脸庞,还是那样冷冷的,只是同“走资派”叔叔伯伯们说话时,才有一丝笑意。我们不敢表达想法,但只要父亲高兴,我们也就高兴了。
寒冬过去,阳春三月。我跟在父亲身后,赶着两头黄牛,从人委(即政府,现玉屏宾馆处)经衙门门口、银行门口、桂花树边、体育场、下巷子、上巷子,穿过南门的古城墙门洞,向城外走去。艳阳高照,水田里波光粼粼,荒丘处处长满了嫩绿的野草;巍峨的东门坡和南门坡苍翠碧绿,坡脚的酒厂,冒出淡淡的烟雾。两头牛随意地在荒丘上吃草,我跟着父亲爬上了破败而杂草丛生的古城墙。
也只有这时,父亲的脸上才没有冷凝,现出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情,比这暖意融融的春色更加让人开心。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说,该吃午饭了,饿了吧?我点点头,却又不敢直说,因为心里清楚,牛还没吃饱,我们此时还不能回家。父亲从衣袋里掏出半斤粮票和三角钱递给我说,去买几个馒头来吃。说罢,又衣袋里掏出手帕递给我,说拿它去包馒头。
我兴冲冲地往城里跑,来到中华路银行门口的那家小食店,买了十个馒头。馒头很小,也就鸡蛋样子,一两粮票六分钱买两个;十个馒头,全包在一张手帕里。馒头热腾腾的香味,从手帕的纱眼里飘逸出来,钻入鼻孔,沁入肺腑,馋得我直咽口水,我舍不得先尝一口,生怕这一尝,就一口气轻轻松松将十个全部吃光。我一路小跑很快就跑回了父亲身边,他看着满头大汗的我说,别这样忙呀,摔倒怎么办?他伸手给我抹去脸上的汗水,接过包着馒头的手帕,解开,先递一个给我。我接过来,一口塞进嘴里,似乎还没来得及咀嚼,就吞咽进了肚子里。父亲笑了,说,傻孩子,慢慢吃,小心噎着。我窘迫地望着父亲,表情一定是又兴奋又羞涩。父亲笑着又递一个给我,他也拿着一个,笑笑的也是一口就吞了。我们两个就这样笑着轻轻松松地吃下了十个小馒头。我咂咂嘴,舔着手指头说,馒头真好吃,爸爸,河南老家是不是天天吃馒头呀?他微笑着点头,但片刻,他收敛起笑容,脸上的表情一下冷凝起来,像涂了一层寒霜,一双眼睛从城墙的断砖烂瓦上向空旷的荒丘望去。良久,他慢慢收回目光,凝重地说,爸爸可能不得再上班了,要被送回老家去,我们全家都回河南老家,好吗?我不知怎样回答,我虽然想吃馒头,但父亲的表情明显告诉我,这回老家该是一种多么被迫的难过啊。没有回答,可我心里却坚定地说,爸爸,随便去哪里,只要有您在,我都愿意。
太阳偏西了,牛吃得差不多了。我和父亲赶着牛往回走,步子怎么也没有出来时那么轻盈,很沉重,就正如太阳要沉到那山下似的。
(三)
又是隆冬,一天下午,天空飘着毛毛雨,寒风冷冷地吹着,我又去“牛棚”。父亲手里拿一根钎担,钎担上捆着棕绳,正跨出门来。父亲说他要到七眼桥那边的坡上去挑苕叶,要我赶快回家,别在外面吹风淋雨。我犟着说要同他一起去挑苕叶,起初他不同意,见我执意,也就任我同他一起。
寒风伴冷雨打在脸上,生生地痛,像针扎一样。我故意装得没事一般,生怕父亲撵我回家。从四眼塘边的县委院子里出来,顺着泥泞的马路,就往七眼桥那边的山坡走去,有三四里路,我们可能走了半个小时,过了桥,上了长长的拐弯坡,再走向路边的黄土坡上。那是一大块苕地,苕挑走了,还剩一些苕叶,散乱地丢在地里。
我帮着父亲收苕叶,将它长长的苕藤顺着理整齐,捆成两大捆。寒风冷雨,手一会就冻僵了,我拢在嘴边哈热气,脚也不停地跳动。哪里跳得动,鞋子上沾得厚厚的泥土,像一个大泥坨子,根本就不能动,移动步子都很困难。我的鼻子肯定冻得通红,我感觉得到,清鼻涕从鼻孔里流出来,唏唏地冷。父亲在加快速度,目的是尽快得以返回,光秃秃的山头上寒风呜呜地吹,实在是太冷了。父亲的额头却冒出热汗,他是戴着斗笠上山的,现在要挑苕叶,不方便,他干脆将斗笠捆在了苕叶上。他用钎担先插进一捆,用力举起一捆苕叶,调过钎担头来,用肩抵着重压,将钎担的另一头插向那一捆。他躬着腰,咬紧牙关,使劲地站了起来,一步步走出苕土。路很滑,真担心父亲滑倒。父亲没滑倒,我却一屁股滑坐在稀泥地上,在地上梭了一溜,裤子全是泥,两只手也满是稀泥,半天没爬起来。父亲放下肩上的担子,赶忙把我拉起来,顺手挽了一把苕藤叶,在我的手和裤子上衣袖上擦着。反正是擦不干净的,擦了一下,父亲就又费力地挑起苕叶,慢慢往山下走。
好不容易到了马路上,虽然泥泞,但路面宽敞多了,也不像山上的黄泥那么滑了。父亲的步子大起来,肩上的钎担,一闪一闪的,两头的苕叶,有节奏有韵律地上下晃动,真好看,优美又协调。突然,嘎地一声响,父亲肩上的钎担断了,两捆苕叶叭地掉在路上。父亲喘着粗气愣了愣,弯下腰去,试图一只手搂一捆,挟在腰间就往回走。太吃力,也用不上劲,根本就挟不住,没走几步,两大捆苕叶就掉落在地上。这一下,加上刚才掉在地上,两捆苕叶全是稀泥,就是想挟,也挟不起了。父亲直叹气,望着慢慢黑下来的天,无可奈何地摇头。我站在一边,什么办法也没有,话也不敢说,全无任何能力帮助父亲,也只有跟着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远处的城里已亮起灯光,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着饿了。毛风细雨,身上瑟瑟地冷,只想快一点快一点回家。父亲看着两捆苕叶,情知无能为力,便将一捆抱起丢在路边的沟里,随手扯了些枯草盖在上面,折转身来,用断了的半截钎担翘起一捆,扛在肩上;叫上我,就躬起腰一步步回走。他的步子不像刚才挑着担子那样富有韵律,而是很吃力,像背负着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得他像一只大虾。我很心痛,痛得只怪自己一点本事也没有,就像一个窝囊废。
我踽踽在后,完全像一个从稀泥塘里爬出来的泥人,父亲浑身上下也都是泥,就是肩上的苕叶也像是一捆泥草,看不出除了泥巴以外的任何颜色……
天,黑沉沉的,也湿漉漉的。我看不清父亲的脸色,看不清他满脸的汗水雨水,也看不清他喘出浓浓白雾的呼吸,但知道,他很吃力,真的,很吃力……我的心,又湿又冷。
几十年了,还是这样冰冷和浇湿,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浮出那风雨泥泞的夜晚,浮现父亲那艰难与疲惫的身影。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