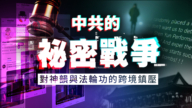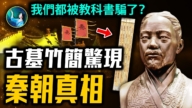【新唐人2012年9月15日讯】在9月10日中国第28个教师节里,直面义务教育的问题,盖过了形式大于内容,鲜花盛开的教师节。腾讯网做了一个专题:“阎锡山治下的山西义务教育奇迹”,其中展示了山西省教育厅1933年编印的《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可见1932年,各县教育经费占当年行政总开支的比例高达 50-60%多。此外,山西政府用于乡村小学的经费,远远多于用于城镇学校的经费。在1920-1924年村立学校经费占全省义务教育总经费的 80-90%。
事情的起因始自《长江商报》记者在9月3日一篇题为《扛着课桌去上学》的报导。它端出了湖北麻城市顺河镇3000多名学生背着课桌报名上学的情景。对此,麻城官员的回应竟然是:“财政挤不出钱来”。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可就是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爆炸,财政收入在过去 20年以比GDP增长率高得多的两位数增长的土地上,偏偏有很多地方穷教育、苦孩子。学校里几十年没有课桌,如今,儿子要背着父亲儿时用过的课桌去上学。说起来,麻城是国家级贫困县,然而,这是怎样一个贫困县?政府有富丽堂皇、号称白宫的办公楼;市委书记杨遥拥有不止一只名表;政府计划投资5亿建设移民公园,花2000万进行绿化升级。就在上个月,8月份,麻城市统计局宣称,其财政收入等7项经济指标“居黄冈第一”。这个吃国家贫困补贴的麻城,盛产以权捞钱的贪官。三年前,市委书记邓新生受贿数百万被双规;副市长被双规。
很难想像麻城政府官员怎么能对小孩子背着沉重的课桌去上学熟视无睹,心安理得。国家扶贫款,为什么不先用在义务教育上?麻城的公款吃喝、公车开支、出国公干的花费究竟是多少?它的教育经费和三公支出是个什么比例?为什么没有监督执法?它当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这个官僚制度及其豢养下的官员,注定是只牟取私利,无心公共服务。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麻城,师资青黄不接,教育质量下降,几年前“撤点并校”的政策,使得教育资源被集中到镇上,村子里穷困得难以为继。从上到下来自财政的教育资金被截留、侵呑、挪用。义务教育法既无尊严也无保障。也是在湖北,几个月前《中国青年报》揭露过,那里补助农村义务教育的资金被“吃空饷”。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拨付的用于教学一线和学生头上的补助金,其实是基层教育部门瞎编虚报骗来的,然后再将它们分掉。可以断定,中国绝不止一个麻城,一个湖北。
1986年,中国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第六章“经费保障”上,有“三个增长”规定:一是各级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二是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三是,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在实际中,这三个增长根本没有保障。
后来,1993年,政府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又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将近20年过去,连21世纪都走过12年了,这个原本上世纪应该达到的比例依然落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2009年中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2.4%,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当然是没有监督。然而,分明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个监督机构,叫教育督导。在《国家教育督导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还明文规定了教育督导的内容,包括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和均衡发展状况;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和使用效果;学和生活设施、设备配备和使用情况等等。问题是,谁来督导?如果是出自教育管理部门的人,自我监督,岂不形同虚设?!
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通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实施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预计今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将达到 2.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虽然这个比例来得太晚了,且和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从绝对值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然而,怎么把它们切实用到实处?如何解决城乡之间、发达和落后地区之间,同一地区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教育经费和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均衡,怎么防止各级政府部分及官员侵吞、挪用教育资金?答案是:不改变现有的制度,无解!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